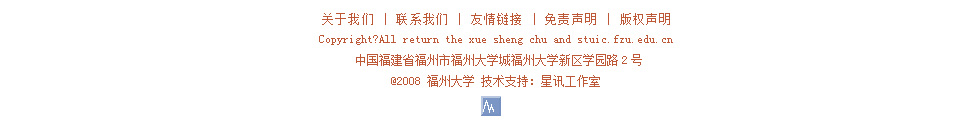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 杨解朴
编按:在2017年第19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两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创下二战以来最差的成绩,而成立仅四年多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率第三的成绩挺进联邦议院,打破了二战后从未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联邦议院的纪录,从而使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首次在六个政党间进行分配。这一选举结果不仅给德国新政府组阁带来困局,导致德国政局连续数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同时折射出德国政党政治生态发生又一重大变化:传统主流政党的凝聚力、支持率下降,民粹主义政党逆势而起。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一变化给德国和欧洲未来带来的影响,值得重视。
德国政党政治生态的变化是伴随德国的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发生的,并且被危机性事件激化,联盟党和社民党因此遭遇选民流失,而德国另择党从中获益。
一、中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淡化造成主流政党选民流失
二战后,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德国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同,不具备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只是以一定收入划分的社会人群的聚合。他们的政治取向与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很大不同,大部分人以个人主义为导向,没有形成明确的代表集体意志的政治主张和阶级认同,通常只是在选举中根据候选人和政党的某些具体政治方案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主流政党为了选举胜利,在意识形态、竞选主张等方面不断趋向中间。然而,各大政党趋中的意识形态虽然吸引了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但也带来了部分选民对政治的冷漠,甚至是厌倦,相似的竞选议题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主流政党的组织形式与参与机制较为落后,对中产阶级缺乏吸引力。中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对政治厌倦的情绪造成了主流政党选民的流失,并且为“标新立异”的政党提供了选民的土壤。
二、危机性事件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带来负面影响
欧洲国家连续遭遇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危机性事件后,德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在欧债危机中,一些欧盟国家的支付能力受到挑战,经济趋向衰退。为了阻止危机,德国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并坚称它在政策上“别无选择”。而德国另择党则认为还存在其他的方案,并提出废除欧元、重新启用德国马克或者建立一个小型的货币联盟等替代主张。一些德国民众认为自身不应承担南欧的债务负担,对德国政府用自己的钱为邻居埋单感到愤怒,支持德国另择党“反欧元”的政策主张。
难民危机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仅给德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融入压力,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不安全感和心里不平衡感。伴随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间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价值观、安全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是造成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诱因。德国在难民安置方面的政策以及向难民提供的待遇又会激怒底层的德国民众,他们认为难民作为德国福利国家的“局外人”抢占了他们作为“局内人”的利益。由于打出抵制宽容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反伊斯兰主义的口号,在难民危机中德国另择党的支持率迅速攀升。而且,近年来,德国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击又往往与难民问题相关联,对于政治精英及主流媒体所信奉的“政治正确”造成很大冲击。
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的夹击下,德国民众的恐惧感与担忧上升,对德国政府处理危机性事件的做法表示不满,造成部分民众转投德国另择党的阵营。大选期间的民调显示,79%的民众认为财富没有被公平分配;88%的民众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真正地公平分配;55%的德国民众认为联盟党忽视了难民政策给民众带来的忧虑;62%的民众担心未来犯罪行为会急剧增加;38%的人担心太多的外国人来到德国;61%的德国另择党的选民支持该党的原因是对其他政党失望造成的;70%的民众认为德国社会日益彼此疏离。
三、现代化、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效应为德国另择党提供了选民基础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下,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全球流动,德国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面临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球竞争力。其结果是造成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低技能劳动者提前退休或长期失业。这些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对于全球化、外来移民会表现出一种抵抗和敌视的态度。他们认为资方和媒体一直在谈论德国缺少技术劳动力、需要技术移民,却没有合适的工作提供给他们——这些德国福利国家的“局内人”。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许多德国民众认为欧盟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加剧,不但体现在经济、财政一体化领域,还体现在移民、难民政策领域。当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的时候,社会成员之间就会在继续推进积极的全球化还是回归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上的保护主义两种路线之间产生分歧。而那些在全球化浪潮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感到被忽视、被伤害的群体恰好在德国另择党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抗议声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在2017年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另择党不但没有发生选民流失,还从其他阵营吸收了378万选民。这些选民选择支持德国另择党的主要原因是对其他政党的失望和不满,民调显示,49%的德国另择党支持者认为,与其他政党相比,德国另择党更能够理解许多民众的不安全感。
四、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的选民成为德国另择党的追随者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导致部分中下阶层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贫困化、下层群体人数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2016年德国贫困人口比率高达15.7%,而2005年这一数据只有5.5%。德国另择党的支持者往往是那些原先支持主流政党,由于职业危机或生活危机造成其社会阶层降低的原中产阶层。这些人不仅存在于工人之中,也存在于受高等教育的阶层中,不是基于特定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基于社会阶层的归属,而是基于社会阶层向下走的趋势,其中部分人是由于福利待遇的丧失,更多的是由于特定群体的权利或说是特权的丧失。2017年大选期间的统计也印证了这一点,德国另择党的选民遍布各个年龄层次和职业领域,男性居多。
在2017年的大选中,德国另择党在东部德国的得票率远高于西部也是一个例证。德国统一27年后,东部德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西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比西部低20%,百姓生活满意度调查也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在这种背景下,虽然东部地区的难民数量实际上远低于西部,但民众对难民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因为在从事简单工作方面,难民与东部地区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民众形成了竞争。另外,东部地区年纪大一些的民众在两德统一后经受了人生断裂式的发展,他们内心往往有一种被忽视、不公平的感觉,存在不满和焦虑。在上述背景下,原主流政党的部分选民转而投身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择党的阵营,造成德国另择党在东部地区支持率达到21.5%,其中在萨克森州甚至达到27%,成为该州得票率最高的政党。
那些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的民众认为作为德国社会的一员,作为德国福利国家的“局内人”,相对于外来移民和难民,他们却被忽略了,他们认为自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输家。他们希望借助德国另择党找到批评社会的机会,他们的失败应被视为社会问题。德国另择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民众的心理,将这些民众的挫败感转换为集体愤怒,并且为他们描绘出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愿景,使得这些民众在追随德国另择党的道路上找到归属感。
(摘自《当代世界》2018年第3期《德国政党政治生态变化的原因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