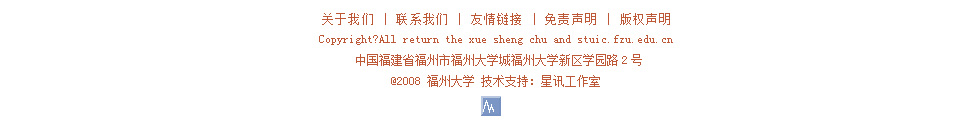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左传》记“(鲁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这短短的几个字,记载了中国法律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即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将以往秘藏于官府的刑书铸在了鼎上并公之于众,以此为郑国的“常法”,史称“铸刑鼎”或“铸刑书”。说这是在法律史上划时代的举措,是因为以往的法律并不公之于众,用现代的法律发展观来解释的话,就是“郑人铸刑书”之前的法律尚处在习惯法时代,而其后法律进入到了成文法时代,“郑人铸刑书”是中国由习惯法进入成文法的标志性事件。
《左传》大篇幅地记载了当时的晋国贵族叔向给子产的书信与子产的回信,这在《左传》及一向惜墨如金的古代史家作品中都是十分罕见的。通过叔向给子产的信,我们知道叔向是反对子产铸刑鼎的,叔向说,自己本来对子产为政寄予厚望,但看到子产竟然不顾历史传统而将刑书铸在鼎上公布时,厚望顿时变成了失望。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天下大治的先王时代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所谓“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就是刑律中并没有固定的罪名,一个人的言行若违背常理或习惯,则由通晓历史掌故的贵族们议而定罪,罪与非罪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全凭审判者们酌情裁定。由此,可以推断春秋战国以前的罪与非罪是没有严格区分的,同一种言行,在此人为罪,在彼人或许就不为罪。处刑的轻重也是没有确定性的,同一种言行在此人被处以重刑,在彼人或许就被处以轻刑。但审判者的“议而定罪”也并非全然没有根据,议定罪与非罪、重刑与轻刑的依据全在于礼,即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与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这种罪与非罪的模糊、重刑与轻刑的不确定,其实正中当时统治者的下怀。如后人解释的那样:刑律不公布,罪名刑名不确定,反倒使法律无空隙可钻,民众对“刑”就会心怀畏惧,日常的言行也就会格外谨慎,这便是“(民)不测其深浅,常畏威而惧罪。”叔向给子产的书信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信息:其一,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法律一样,中国在成文法出现之前同样经历了一个习惯法时代,由习惯法发展为成文法或法典是法律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例外。其二,我们还可以知道,习惯法时代的议而定罪,使制度变得简单,一切制度上的疏漏可以由受过贵族教育的审判者来弥补,审判者的“议”决定着罪行的有无与用刑的轻重。叔向很欣赏这种“先王”的制度,所以他以历史的经验告诫子产“国将亡,必多制。”面对这样一封言辞激烈的谴责书信,子产的复信很简单:“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确实如您所言——我能力有限,不能顾及子孙。虽然不能遵循您的教导,但还是要感谢您的教诲)子产简洁的复信同样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那就是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已经是时不我待,而成文法的出现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救世”的必经途径。果然,时隔23年,也就是公元前531年,在叔向家乡晋国,刑书也被铸在了鼎上,予以公布。而随后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变法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公布法律,尤其是刑律,什么样的言行为罪,什么罪处以什么样的刑罚,法律从不确定的习惯走向了确定的条文。
于是,法律从习惯法走向了成文法。成文法时代的特点就是“法官”依法行事,“议事以制”所依据的人情世故从法律中被挤压出去。《韩非子》记载了春秋时期一则“楚昭侯罪典衣与典冠”的案例,反映了法律公布之后的执法情景。韩非子记,有一次楚昭侯喝醉了酒,迷迷糊糊地睡下了。典冠——掌管君主帽子的官——看睡梦中的楚昭侯似乎有些寒冷的样子,于是就将楚昭侯的衣服给楚昭侯盖上。暖暖和和的一觉醒来,楚昭侯心情很好,便问周围的人:“谁为我加衣?”(谁给我盖上了衣服?)周围人回答:是典冠。出人意料的是,楚昭侯同时处罚了“典冠”和“典衣”(掌管君主衣服的官)两个人。处罚的理由是典冠“越其职也”(越权),典衣“失其事也”(不作为)。韩非盛赞楚昭侯能不以个人的得失而依法而行。依法行事而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就是“法治”(成文法)时代区别于礼治(习惯法)时代的最大特点。
但是,成文法时代碰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稳定的法律与变化的社会之间似乎有着无法调解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说,法律一经公布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现实却变化无穷。为了调和稳定的法律与变化着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会不断颁行法律来弥补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立法上的空白。于是,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成为一个法律迅速膨胀的时代,也成为历史上法律最无人情的时代。楚昭王对典冠与典衣的处罚就是一个例证。
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成文法时代伊始,在克服习惯法不确定之弊病的同时,人们也感到法律过于机械僵化的不足,如楚昭侯一类的做法虽然得到法家的盛赞,但更多人对此也许有一种无聊或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在“议事以制”的习惯法背景下,为睡着了的王加衣的做法是不会受到责罚的;还因为就人情而言,为王加衣的典冠是出于一片好心,而且效果也不错,法律怎么会处罚出于善意且行为有效的人?但成文法却不作如是观,无论典冠为王加衣的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只要违背了法律,就要受到处罚,这确是有些不近人情。这种不尽人情的法律,有时直接威胁到王的安危。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并流传了两千年的“荆轲刺秦王”故事就是一例。秦王嬴政在朝堂之上遇到荆轲行刺,而满朝文武竟不知如何救助——因为秦的法律规定,大臣上殿不得带兵器,而带有兵器的秦王的警卫又都站在殿下,且法律严格规定:没有诏令不得上殿。
当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激变过后,汉人对情与法进行了调整,这就是全面借鉴习惯法与成文法的经验教训,将成文法改造成天理国法人情兼顾的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延绵了近两千年。划时代的社会变革须假以时日方能完善——这就是春秋战国法律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