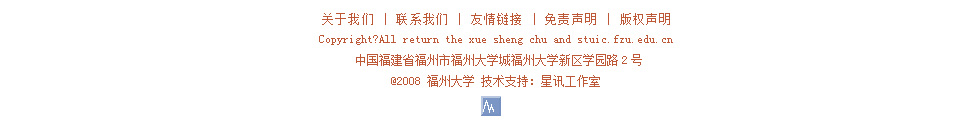2016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开合、俯仰百变。中东的难民潮、不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土耳其的“再穆斯林化”、欧洲反建制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渐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所有令人惊叹的事件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无疑受人们关注。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下,“美国优先”是否可行,正当性基础又何在?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万民法》说:无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个社会边界的划定有多么的任意,但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作为有效代理人,对自己的领土、人口规模以及土地环境的完整性负起责任。马克思、恩格斯的终极理想是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他们也强调,在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到来以前,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形式首先是民族的,他们的斗争舞台是国内。因而,一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合意的。
然而,当下的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机制萌芽于二战后期,形成于冷战期间。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联合国的架构及其运作模式,主要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虽然它在止息人类纷争、增进合作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本质上是强权政治和大国争斗的产物。就程序正义而言,它在起点上就是不公正的。平等尊重各民族、各国家的基本权利,在康德看来是人类和平的前提。这一前提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导出,而是实践理性范畴中的道德义务、绝对命令。不然,人类只能停留在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
为了走出丛林法则统摄的世界,人类需要通过契约建构秩序。世界秩序如果是正义的,那么法则的制定必须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对此,规则制定者事先应当忘掉身份,用罗尔斯的话说必须置于“无知之幕”背后,且不能求助于某些宗教、道德学说所宣扬的“善说”。这样,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这样,各方参与制定的法则才是公平的。
战后国际秩序的型构是一国主导的,其法则是众多国家“不在场”的情势下制定的。所以,战后的国际秩序无论是起点、规则还是过程都存在不对称性。没有程序正义,就难以有实质正义。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后,借助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全球11亿人脱离赤贫。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世界发展呈现极端的不平衡。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主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还带来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所描述的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困境的出现,更多源自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据美国注册的全球生态足迹网新近披露的数据,目前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2.7公顷(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而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9.5公顷。“按美国人均足迹计算,我们需要5个地球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曾经提醒世人,为了避免“增长极限”的到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必须提高这个世界上穷人的消费水平,同时减少人类总的生态足迹。因此,必须要有技术的进步、个人的转变以及长期的视野,必须要有超越政治疆界的更高的尊重、关切和分享。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国际规则和治理机制的合理、公正,它构成了国际秩序的背景正义。背景正义仰赖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仰赖对话基础上的重叠共识。只有背景正义,才能保障《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彰显的推动历史的力量最终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决定历史进程的方向。我们同样可以说,每个民族都在各自既定的文化传承里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世界的历史。显然,国际正义的实现,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都需要罗尔斯所说的“组织有序”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的道义担当。新形势下,所谓大国应当明白自己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有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