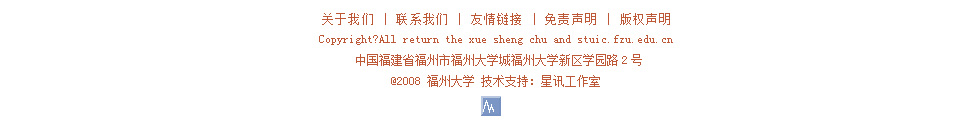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不是有一个安稳的工作,或者将来成什么名什么家,对我来说,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
——陈瑞祥(1966年3月7日)
正是固原最冷的时节。
我们的采访在陈瑞祥的“办公室”里进行,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衣,写一会儿字就要搓一搓手。借来的办公室陈设简单,桌上摆放着老陈正在整理的史料、蘸水笔、碳素墨水、橡皮和两个已经所剩不多的铅笔头,旁边有堆积如山的手稿和档案,那是老陈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文山。
得知我们要来,老陈到门房借了一大壶开水,又匆忙到旁边找了几个杯子,老陈说: “平时忙得顾不上喝水,也就什么都没准备。”
陈瑞祥不善言谈,只用简单的时间表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在他云淡风轻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听到了震撼心灵的故事,听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伟岸与无私。
他就是那位矿井掘进工人,先后四次吐血依然不下火线的人吗?
他就是那位舍弃行政机关工作,宁愿扎根深山,至今仍是初级职称的人吗?
他就是那位每天书写近万字,20多年笔耕不辍,独自编纂固原组织史的人吗?
望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眼中,蓦然有泪。
他内心的阳光如火一样炽热,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在百米深的矿井之下,陈瑞祥如同一面朴素而坚定的旗帜,浩浩然飘扬在自己的阵地上
1968年10月,陈瑞祥做出了人生的第一道选择题,他在教师和矿工中选择了后者,心甘情愿地来到石炭井三矿做起了掘进工人。
掘进是采煤的开路先锋,工作进度直接影响着生产进程。打眼、放炮、出渣、架棚……每一道工序,陈瑞祥总是抢在最前面,甚至在中午吃饭休息的十多分钟,他依然嘴里嚼着饼子,双手推着矿车在通道中奔忙。
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多产煤多进尺”是铭刻在每一个工人心中的信条。在矿山工作,危险如影相随。有时候,零点几秒的误差就有可能天人两隔。
“捅煤眼”是矿井中危险系数最高的工作。煤层在悬空处堵塞,必须有人到下面疏通。疏通后,成吨的煤从头顶上呼啸着砸下来,无异于 “灭顶之灾”。 “捅煤眼”本不是陈瑞祥分内的事,但是煤层堵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这时候陈瑞祥总会说: “就我吧。”之后拎了一把铁锹就走,让工友们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
这是陈瑞祥多次“捅煤眼”动作的一个剪影:一手抓着墙壁的电缆,一手将铁锹用力向上捅,“哗”地一声,他被巨大的冲击力拍到墙壁上。陈瑞祥说:“一只手必须死死拉住电缆,怎么疼也不能放下,否则冲下去就是两三百米深,直接被压在煤堆下。”每次“捅煤眼”,陈瑞祥都会被煤烟染成黑人,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工地时,工友们望着他,哭了。
掘进过程中,经常是血肉与硬石的对抗,石头硬在外表,血肉之躯硬在精神。“硬碰硬”的时刻,血从指甲缝里流出来,疼得钻心。这个时候,陈瑞祥会直接把血手伸进煤渣里,两只手瞬间由红变黑,陈瑞祥说:“煤渣能消毒杀菌。”直到今天,老陈的双手还残存着矿山的烙印,他的几个手指甲全部凸起来,与骨肉分离,在手上耸起了一座座小山。在矿上的那些年,陈瑞祥的十个手指缠满了胶布,黑胶布成了他手指上的第二层皮肤。1973年,离开矿井几十天后,这些胶布才慢慢脱落。
开山破石需要打眼放炮,每一个班掘进过程中要放三四次炸药。炸药库在半山腰上,每天要早起爬到半山腰背药,晚上收工后还要把剩余的炸药送回药库。在矿山工作的那几年,领炸药、连线、收药的工作全是陈瑞祥一个人干。有一次,陈瑞祥在矿洞里连接炸药的引线,他还没有完全连好,一个工友就扳动了炮机的开关。或许,语言无法还原当时危险的场面,那种心悸与后怕只有经历过才能切身体会。陈瑞祥说:“想起来头皮直发麻,要是正负极连起来,炮声一响,骨头都找不到。”
还有一次,为了在泥水中“抢救”一根60公斤重的钢柱,陈瑞祥钻进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的洞里,硬生生将钢柱从泥泞中拉了出来,他的头刚刚从洞口伸回来,煤渣碎石轰然而下。老陈告诉我们:“那次,晚一点就被死神拽走了。”
“您不怕吗?”记者问。
“就怕好好的一根钢柱埋在土里浪费了。”
谁会选择艰苦?一次,两次,三次……把苦的留给自己,把甜的让给别人
1972年春天,因为劳累过度,陈瑞祥吐了四次血。
前三次他偷偷把血迹掩埋起来,依然坚持到井下作业。第四次吐血,吐了有小半脸盆,工友发现后报告了矿领导。领导命令他卧床休息,并派人监督他,躺不住的陈瑞祥还是瞒着领导继续下井。
1972年底,考虑到陈瑞祥的身体状况,矿上领导安排他当电工。电工的活相对轻松,有了事情下井,没有事情原地待命。但是上班号一响,陈瑞祥又跟工人一起下井,一起干活,电路有问题他再跑去处理问题。矿领导的本意是让他轻松些,没成想又给他的肩上多加了一份担子。
在矿上工作的那些年里,陈瑞祥没休过一个病假,没旷过一天工。1968年至1975年间,陈瑞祥只回过三次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靠妻子一个人承担,妻子怀孕时他没能在身边照顾,大女儿出生半年后,他才见了第一面。
1973年5月20日,陈瑞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作为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陈瑞祥当选为自治区团委第四书记。在团委工作期间,只要周末有休息时间,他想的不是回家与妻儿团聚,而是坐车回到矿上,干上一个班的工作。
一个用爱去工作的人,身体里藏着无限潜能。
陈瑞祥爱他的煤矿,虽然身份已经是行政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却时时要求再回到矿上,为了这份难以割舍的牵挂,他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从矿上转出来。有人笑话他傻,留在自治区团委前途无限,为啥还要回那个地方受苦受累?陈瑞祥说:“到了矿上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熟悉得不得了,亲切得不得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78年9月,自治区第四次团代会结束,陈瑞祥继续向组织申请要求回到矿上。陈瑞祥辗转得知,固原王洼煤矿开始筹建,他找到有关领导申请到王洼煤矿工作。领导问他:到王洼煤矿,你的职务要降几级,怎么办?陈瑞祥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别的我都不考虑。”
1978年11月1日,陈瑞祥来到王洼煤矿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的临时负责人,干部职级成了科级。
1979年,王洼煤矿列入国家缓建行列,煤矿筹备各项工作全部停了下来。阴差阳错,老陈与自己的矿山梦挥手作别。得知煤矿缓建的那天晚上,陈瑞祥第一次流泪了,他那颗想为煤矿燃烧的心被泪水打湿。
采访中,我们问老陈:“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再让您回王洼煤矿,您还会去吗?”
老陈轻轻说了一个字:“去。”
工作中的陈瑞祥如同一颗火种,放到哪里,就在哪里燃烧。一部固原组织史,浩浩汤汤百余万字,字字凝血
王洼煤矿缓建后,陈瑞祥陆续在固原卫校、固原地委办公室工作。1986年,调入固原地委组织部,4个月后,还是组织系统新兵的陈瑞祥接到一项重要的任务——担任固原组织史编纂主笔,编写1932年至1987年的固原组织史。
当时全国组织史的编写工作刚刚展开,没有任何成品可以借鉴,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人和事尘封已久、早已物是人非,隔着半个世纪的光阴,陈瑞祥困惑良久。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收集资料的最初时期,陈瑞祥每天泡在档案馆里,“一沓稿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坐天黑”,边查阅边记录,几乎用笔抄录了半个档案馆。固原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马秀琴回忆:“老陈是档案馆的常客,一查资料就是一整天,下班了需要催他几次才起身离开。每次老陈过来,我们都会给他倒一杯白开水,走的时候开水变凉了,却一点都没有少。”
50多年过去了,曾在固原各级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都已离开,居住在广东、河北、吉林、北京、黑龙江等地。为了向他们核实有关情况,陈瑞祥记不清自己发过多少信函。为了确保史实的准确无误,每一次都需要向当事人提供一份详细的询问提纲,写明每个事件的过程、需要解答的问题。1936年6月至10月,慕纯农担任固北县委书记,退休后慕纯农身居北京,陈瑞祥先后五次发函,历时半年之久,终于将当年的史实弄清。在厚重的固原组织史中,这样的当事人有近百名。
1990年冬天,陈瑞祥的父亲因病住院。那段时间恰是审查修改各县区组织史稿的关键时期,如果耽搁一天就会影响整部书的编写进度。晚上到医院陪护父亲时,陈瑞祥总不忘揣上一摞书稿。安顿父亲睡下,病房熄灯后,他从护士办公室借来一把椅子放在楼道,在昏暗的灯光下,以腿为桌,一字一句修改书稿。
1991年底,书稿完成交付印刷时,陈瑞祥把办公室搬到了印刷厂,40万字的书稿他整整校对了5遍。每一遍,他都要逐字逐句认真审读,每一个时间、机构、人员都要一一斟酌核对。因设备的限制,每处的修订不能直接在原稿上涂改,只能另找一张白纸把需要改正的地方写出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再由印刷工人对照修改。5遍校对下来,仅仅是修订稿就是厚厚的几大摞。
一部组织史,浩浩汤汤百余万字,字字凝血。
那五年里,
陈瑞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他办公室的灯从未在夜里零点之前熄灭过;
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头发大把脱落……
当时,一个地区的组织史涉及党的系统组织史、政权系统组织史、军事系统组织史、统战系统组织史、群众团体组织史五个部分。在其他地区这五个部分分别由3-5个人分别承担,而固原地区组织史基本由陈瑞祥一个人编写,与其他地区同步完成。根据测算,其他市县编写的组织史最高的地方每个字的成本在0.3元左右,而陈瑞祥编写的固原组织史,每个字的成本仅为0.1元。
1992年11月,中组部要求各地续写组织史,续编本时限为1987年11月至1993年12月,并在续编本中增加企事业单位的部分。这项重任又落到了陈瑞祥的身上,他一边征集资料一边编写修改,用3年时间完成了16万字的续编任务。
那个干起活来从头到尾不歇一口气的人,是他;那个较真认死理分毫不差的人,是他;大家说:陈瑞祥是这个时代的“稀有动物”
在固原市委组织部,提起陈瑞祥,大家都会亲切地称他为“陈老总”,因为他是组织工作的“政策通”、业务工作的“活字典”。在组织部的20年里,陈瑞祥从事过很多工作,在同事们的记忆中,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多么细小的工作,陈瑞祥总是兢兢业业,从无怨言。
植树造林中干起活来从头到尾不歇一口气的人,是他;到扶贫点工作从来不要求单位派车,自己掏钱坐班车的人,是他。大家说:陈瑞祥是这个时代的“稀有动物”。
2005年,陈瑞祥退休。卸下琐碎繁重的日常工作,辛苦半生的他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但是在老陈心里,始终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闲不下来的老陈找到市委组织部领导,要求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将组织史续编延伸至2008年。在固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金元的办公室里,老陈动情地说:“共产党人永远没有退休可言,能完成组织史的续编工作,我这辈子死而无憾。”这句话,每个字都敲在马金元的心上,望着这位退休不退责的老组工干部,马金元震撼了。
当组织部办公室询问老陈需要什么帮助,陈瑞祥只要了三样东西:墨水、稿纸和两包烟。老陈自己不抽烟,他要烟是为了方便征集资料,递上一支烟就能打开当事人的话匣子。
在借用的办公室里,年过六旬的老陈躲进小楼,一心一意扎根在故纸堆里,坚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没有人催过他一天,也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过任何要求,但陈瑞祥给自己确定了明确的 “时间表”,他将书稿完成的时间定在2011年3月。
采访时,老陈愧疚地说:“从2009年到现在,因为中途旧房拆迁、买房子、装修,自己生病住院两次,把时间耽误了,要不是因为这些,书稿去年底就能完成。”
一番话,把我们的心弄疼了。
这是怎样一个老人啊?需要何等的坚定,何等的执著,何等的信仰,才能抵达那种高度!那种境界!
每天查资料、寻访当事人,老陈总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老陈的家到固原行政中心,一天来回四趟要二十余公里,办公室主任杨秀鸿看到老陈辛苦,就给他办了一张行政中心的公交月票。老陈却说:“我每个月只上来十五六次,如果我用了就会浪费一半,公家的便宜咱不能占。”
白天,老陈在旧稿纸上抄抄写写,晚上他再把白天整理好的史料誊抄在新稿纸上。老伴埋怨他:“白天写晚上写,家里的台灯泡不知换了多少个。”亲戚朋友不理解他:“退休了还让自己那么辛苦,你图的啥?”陈瑞祥说:“啥事情也不能从名利的角度看。多少离退休的人打麻将、遛鸟,我却恨不得一天当三天用,一个小时当五个小时用。”
按每个小时1500字,每天书写12个小时计算,老陈一天就要写上万字。如果文字也能像砖块一样码成建筑,那么老陈20多年笔耕不辍早已完成了一座万里长城!
“陈瑞祥个子不足1.7米,但面对他就像面对一座高山,一座道德的高山,一座精神的高山。”
工作了半辈子,陈瑞祥至今仍欠着十余万元的外债。
2009年,老陈在固原城区买了房子,贷款11万元,装修时又跟亲戚朋友借了3万多。退休后,陈瑞祥每个月的工资三千多,老陈说:“还贷款一千多,给老伴买药一千多,再加上日常开销,几乎剩不下什么。”
老陈档案表的职称一栏至今都是助理编辑,初级职称。陈瑞祥说:“跟很多同龄人比起来,我的工资不如人、职务不如人,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很舒坦的,因为我实实在在为国家、为党做出了一点贡献。”
陈瑞祥的老伴种着三亩菜地,直到老陈退休,老伴耿秀英的身份一直是个卖菜的。这么多年,耿秀英为了抚养儿女照顾老人,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病,时常头疼,经常要到诊所做理疗。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老陈的儿女陆续长大成人,他稍稍动一动脑筋就可以把几个孩子安排好,但是老陈从来没有跟组织提过任何个人的难处。至今他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工作,小儿子退伍后转业到了一家冷门单位。
陈瑞祥一生演绎了两个“角色”:在百米深的井下,他是精神的掘进者;在成山的故纸堆里,他是一个人的史话。
采访过陈瑞祥的固原市电视台主持人李玲说:“作为一个‘80后’,我一点都不理解老陈,但是通过与他长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他是我长这么大认识的最合格的共产党人!”
也许,老陈稍稍自私一点,他的人生轨迹就可能远离平凡与琐碎。但是老陈却说:“忙起来家里的事顾不上,老婆孩子埋怨,个人的事都是小事,都可以克服;党的事是大事,不能耽误。”
抱怨归抱怨,采访时我们向耿秀英问起老陈有啥缺点,她淡淡地笑着说:“好着呢!”
采访结束后,天已经黑了,陈瑞祥送我们出门,天正冷,迎着风,身后老伴捧了一件棉大衣撵出门,披在他的身上。这一幕,如雕塑般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一个问号从心底悄然升腾:
幸福究竟是什么? 文章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