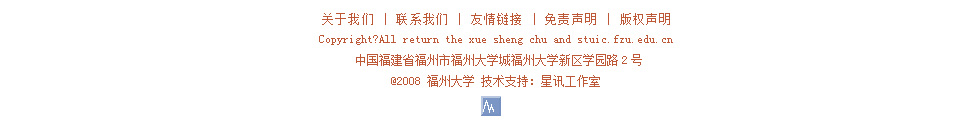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
“雷锋热”卷土重来,很多地方开始“常态化”学雷锋,如长沙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对学雷锋先进人物给予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政策优先;北京每周六为学雷锋日;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将“学雷锋”纳入学生考评等等。随着宣传,在网络和微博上雷锋也被推上了“质疑”的风口浪尖,有人质疑雷锋当年事迹、日记和照片的真伪;有人质疑灌输式和功利化的学雷锋,效果是否会适得其反;也有人质疑学雷锋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矛盾。其中任志强的质疑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雷锋出现之前,中国文化靠的是什么?”
在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真实从来都是最高主题。因为只有从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我们才可能真正去学习与获益。给一个人贴上善恶、好坏的标签很容易,但如果对当事人的心理事实不了解,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境况没有分析,对当年整体的精神和社会现实没有判断,就轻易得出学习或否定的结论,显然都失之偏颇。对雷锋这样一个“榜样”人物,就更是如此。因为个人总是处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中,无法抽离时代而孤立地存在。尤其对那些左右个人善恶的特殊历史原因,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同样无法把握一个人的精神脉络。即使去学,学的不过是一个脸谱化、标签化的典型,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从已披露的雷锋日记来看,雷锋显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的也多是一些平凡小事。但在媒体宣传中,他总显得遥不可及,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困惑。在传统国家,人们常通过推崇英雄或伟人的功勋和精神,来引导青年理解历史和生命的价值。但进入现代社会,对英雄和伟人总是加以提防,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去魅”,一方面去除了天道、报应、神恩之类的观念之魅,一方面也去除了英雄、伟人的偶像之魅。因为不除巫去魅,人就会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自然影响到公民意识的形成与成长。所以现代社会只有历史人物或名人,即便有伟大的人物,也是指那些在思想殿堂有创造、有历史贡献的人,因为他们的卓越思想、社会行动、科学或艺术成就,有助于公民塑造自身平等理性、自由包容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我们也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名人越来越多。与神、圣人、君王或政治偶像比起来,名人的“毒副作用”要小得多。名人好歹还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丢丑跌份的时候。因为神、君王、救星的衰落,才有了名人的繁荣,它其实是社会走向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广阔的公共生活,呼唤各类名人,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来说,它也是一贴能解毒去魅的膏药。名人总是与民众连在一起的,没有民众追捧,名人便丧失了地位。但民众情绪的变幻无常,注定名人的影响力只是一时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再难塑造全社会共同学习的英雄的原因。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他的真实、鲜活,因为他对苦难历史的见证,或许能让我们格外体会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尊严和价值。抛开那些强加给雷锋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或许可以听到来自历史深处另一种真实的声音。有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思考,我们对当下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才会有一份更为清醒的认知。
今天说起雷锋,人们大多想起的还是他的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实质上这是一种很原始的道德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佛教说“行善得报”,表达的都是这种原始道德观。如孟子所说,这些都属于“不学不虑”就有的“良知良能”,就像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本然之善。只要社会不对人性进行损害和扭曲,人的本性中就有这种秉赋。现代社会,显然对一个公民的道德观有了更丰富的理解。除了肯定良知良德的价值外,还多了分享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理念。 [FS:PAGE]
现代社会不会强求公民必须“无私奉献”,一种成熟的公民意识会在关注自我利益、帮助别人之外,主动去促进公共利益的进步与发展。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他们或对国家事务进行辩论,或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或对弱势群体展开救援,或对政府决策发表公开主张。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把公共权力看作控制与服从的关系,而把公共领域看作一个平等、协商、合作的互惠空间时,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自治状态。这些观念显然是雷锋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具备的。
现代社会助人为乐的理念同样变得更加丰富。公益和慈善的“助人为乐”,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更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现代社会,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福利有同样性质,政府会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民众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如何从立法层面保证给民众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变得更为重要。这些理念,显然也是当年的雷锋所无法理解的。
雷锋生活的时代远去了。与其去学习那个遥远的雷锋,不如先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雷锋,进而学习雷锋身上的那些“小道德”。这样,世界才能更美好。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