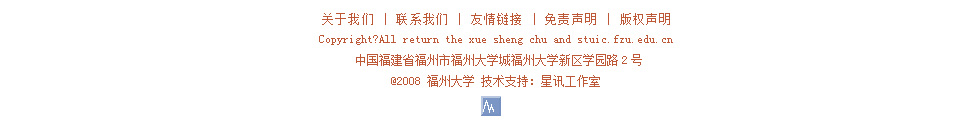如今的我已经步入中年,可是儿时的某些记忆依然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这些记忆被我封存在脑海的深处,虽然时隔多年,偶尔想起我依然能品味出其中苦涩和辛酸的滋味。
大家可能看过宋丹丹和黄宏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大家看过后,哈哈一笑,只当那是个笑话。而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家真实的写照。在70年代的农村,没有儿子会被别人说成“绝户头”。在父亲被邻居骂为绝户头后,父亲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个儿子。1979年三妹出生后,父母就被迫踏上了漫漫的“超生游击队”之路。
父母和奶奶姑姑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粮食都偷偷的藏到好心的邻居家里,父母便带着三妹躲到30里外的姥姥家。我和姐姐在家里跟着奶奶。那时我也就三岁多点。镇计生办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把我家的房子给扒了。扒了我家的房子后,依然找不到我的父母,在那个计划生育大于天的年代里,这是不能算完的,又要扒我奶奶家的房子。村里人好说歹说的求情,说房子如果扒了,我奶奶爷爷还有姑姑们这一家老小上哪儿去住哪?计生办的人才没有扒我奶奶家的房子,而只是把房顶的瓦给揭走了。我永远记得揭奶奶家房顶时的情景,奶奶又气又吓,瘫倒在路边,好多人都围在奶奶家看热闹。年幼的我,估计已经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大人我是不敢撵的,我在人群中撵着围观的小孩子。
奶奶害怕被抓到镇上蹲禁闭,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领着我到邻村亲戚家躲避。到晚上天完全黑下来,再领着我回家。因为当时小,实在记不起这样来来去去了多长时间。我们全家犹如惊弓之鸟。村里喇叭一响我们也是闻之色变。每到过年,父亲都是大年三十晚上天黑以后到奶奶家,家里只要一来外人,父亲就赶快躲起来。只有父亲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知道父亲来了,偷偷到奶奶家呆上一会,跟父亲聊一聊。大年初二晚上天黑了以后,父亲再偷偷地赶回姥姥家。
后来计划生育的风声越来越紧,父母不敢在姥姥家住。舅舅和表哥们就在姥姥家附近的河堤上盖了个小土房子,让父母搬到那里去住。河堤白天还可以,到了晚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河堤也很“紧”,附近村里死的未成年人,都是随便埋在河堤上的。在母亲生下小妹后,父母就把小妹交给二舅妈,不远千里,投靠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老乡的家里。后来听二舅妈说,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妹瘦的不成样子,奶也不好好喝,总是长长的叹气。
那几年,三妹和小妹基本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我是偶尔去住一段时间。姥姥家对于我来说,是天堂。姥姥家还算富裕,那时老爷已经去世,姥姥跟着二舅一起住。二舅和二舅妈对我们特别好,有时我们一家5口都在姥姥家住着,二舅妈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对我们一如既往的好。在姥姥家不用干活,吃的还好。大部分时间是与表姐玩耍。我们一起挎着篮子挖猪草,由于贪玩,往往挖不满篮子,我们就用小树枝把篮子的下半部撑起来,把猪草尽量弄得蓬松,看上去像是挖了满满一篮子猪草。挎到家,赶紧把猪草倒到猪圈里,怕大人们看穿我们的小把戏。可是在印象中,也没有谁检查过我们挖了多少,估计是我们心虚的原因吧。夏天的时候,姥姥家北面的大河经常干涸,我和表姐表哥经常拿着盆和水桶,到河里逮鱼。在姥姥家,是我童年最愉快的时光。有时候在奶奶家住着,晚上做梦是在姥姥家,玩的那叫一个高兴,等早上睁开眼一看,怎么是在奶奶家的床上,往往眼泪就流出来了。
在奶奶家,因为我们家乡种水稻,我们都用秋收后脱粒完的稻草编织成草片子卖钱,这也是当时我们农村除了卖粮食唯一的挣钱方式。姑姑们编织草片子,我和姐姐就负责用镰刀头把稻草修剪整齐,我们俗称“剪草”。姑姑们好用修剪好的稻草纺草绳。夏天,我和姐姐在树荫下坐着剪草,邻居同龄的伙伴们都成群结队地到河里游泳玩耍,路过的邻居总是怜惜的说,都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才这么可怜听话。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父母不在身边的苦楚,我小时候就已经尝过。
为了要儿子,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抓捕,不远千里,投亲靠友,历尽千辛万苦。历时4年的时间,直到1983年弟弟出生,父母才带着弟弟“荣归故里”。我依然记得从姥姥家回我家的情景,妈妈抱着弟弟,我和三妹小妹还有二舅家给的只小羊一起坐在地排车上,由爸爸拉着。我记得回家那天天格外地晴朗。
1983年,父母回到家里,房子已经让计生办的给扒了。穷,还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我们没有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都是不合适的。借住在邻居家的房子里,高额的超生罚款,缺吃少喝的困境,我们姐妹们又都开始陆续上学,现在我都想象不出父母面对当时的困境是怎么熬过来的。
三妹干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父母要下地干活,我和姐姐已经上学,弟弟还小,三妹在家负责照顾弟弟,弟弟睡觉了,三妹就把门锁上,蹲坐在房门口看着,从来都不离开半步,怕我们的宝贝弟弟被别人抱走喽。
后来父母借钱盖了房子,我们才从邻居家搬走。由于四妹和小弟是黑户,没有户口,就分不到地,而我们又正是能吃长身体的年龄,家里的小麦每年都不够吃的。可能怕婶子说闲话,奶奶让我们天蒙蒙亮就起床,到她家偷偷背麦子回家。那时,二舅家也时常接济我们。
虽然那时大家都穷,但是我们家比邻居家更穷。每到交学费时,我几乎都是最后一个交的。班主任催了一次又一次,实在没有办法,才鼓足勇气给父亲提交学费的事情,父亲往往什么也不说,提脚出门到邻居家给我借学费。小时候,我们的衣服也是姐姐穿了,我再穿,我穿小了,在给妹妹们穿。小弟和小妹上初中时,穿的鞋子都张着嘴 。我们姐弟五人从不跟父母要吃的穿的,但是那时的我们真的很羡慕同学们比我们好的生活。
为了我们5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学费,父母又承包了鱼塘和果园。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是一点也不假。每到暑假,邻居家的孩子几乎什么活都不用干,成天在家里看电视玩耍,而我们每天长在果园里,拔草、施肥、给果树打药。晚上才有空找伙伴玩一会。晚上看我们的小腿,像穿着黑色的丝袜,黑黑的一大截,那是干活晒的。姐姐那时学习还不错,但是中专没有考上,认为考高中父母负担太重,选择了辍学,跟着父母一起在果园里忙。每年秋天果园收获,一秋一冬地用三轮车带着苹果到集市上去卖。我们当时十四五岁的年龄,已经扛着整筐的苹果从果园里往外运。我每到星期日,也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去卖,早上3、4点钟起床,困得那个难受,气的我总是把盆呀、筐呀的踢得叮当响。等走到集市上,起床气也就消了。
记得一次母亲在公路边卖苹果,不知怎么让蜜蜂误会了,成群的蜜蜂冲向母亲,母亲扔下路边摊,拼命的往果园跑,最后没有办法,跑到稻地里藏起来,蜜蜂才善罢甘休。但是母亲已经被蜜蜂蜇的面目全非。整个头和脸肿的像面包,眼睛肿的都看不见路。
后来我离开家上高中,小妹和小弟上初中。由于父母在果园里忙,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弟弟放学后,就用自行车推着麦麸到鱼塘喂鱼,小妹就开始烧火做饭。有时奶奶会做好饭,让弟弟去吃,小妹是不让去的,因为弟弟是宝贝孙子。虽然弟弟是宝贝的,但是父母对待我们,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一视同仁,从没有偏心过,事事都一样。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一次哭泣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那是刚放暑假,妈妈看到弟弟的小伙伴们,在家里树荫下打牌玩耍,回到家哭着跟父亲说,看看人家的孩子,再看看咱家的孩子,咱们的孩子没有过一天这样的日子。我想母亲当时一定是有感而发,看到别人家孩子快乐玩耍的那一幕一定是触动到母亲内心深处一直存在而没有时间去梳理的感触。其实,在我小时候,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父母不把我们送人?送到比我们家条件好的人家,父母和我们也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前不久回家,母亲还对我说,跟父亲聊起养5个孩子的不容易,父亲还蛮自豪地说,从来就没有过要把孩子送人的想法。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耻。虽然受了这么多的累和苦,虽然为了孩子们付出了一生的血汗,但是父母依然认为这是值得的。
小时候的我,对于这段往事是不能理解的。我一直埋怨父母当初的选择。而今,已经步入中年的我,依然不赞同父母当初的选择。但是现在的我能完全理解他们当初的选择。就是在全国放开二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为了要个儿子,把怀胎中的胎儿一个又一个的打掉;为了要个儿子,喝一付又一付苦涩的中药;为了要个儿子,夫妻假离婚假结婚,偷偷的生偷偷的养。时隔40年的今天,我们有知识有文化,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还依然在要儿子的道路上踽踽前行,更何况40年前我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父母?
我认为,父母的选择没有对错,是处在那个年代的偶然和必然。只是为了这个选择,我的父母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付出了更多的辛苦劳累,付出了更多的泪水和汗水。作为儿女,我们比同龄人经历了更多穷苦和磨难。我只是希望那些年的那些事,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财富而不是我们自卑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