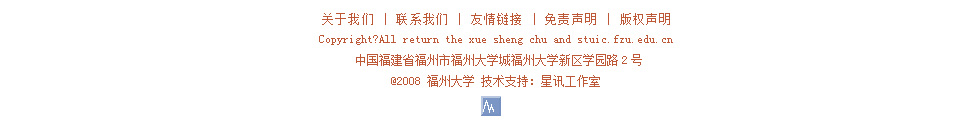中国新诗跋涉到现在,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让诗评者常常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是事实。读李逢忠先生的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总感觉诗人在乐此不疲的浅唱低吟中发出一种声音——澄清,也是事实。
我之所以要说澄清,是因为众多诗歌流派的出现,一方面让诗坛增添了热闹的景象,一方面让众多诗爱者迷失了诗的方向,看不到诗的希望和力量。而李逢忠先生的这部诗集,至少还没有偏离中国新诗作为诗的方向,还没有让诗爱者感到失望。如果中国当下的诗歌,还可以按照“不合乐者为诗,合乐者为歌”的传统办法划分,李逢忠先生的诗歌就应是诗,而非歌。因为诗可以独立于乐曲之外,依靠自身的构建得以支撑,相对歌而言就更为严肃,更注重自身诗味的求索。这种求索包括修辞的使用、意象的选取、情感的张弛、想象的收放、语义的延展、诗意的隐显等。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无疑就在这些方面努力澄清那些属于诗的事实。不过,诗集让我最为感动的澄清当是那些反复出现的意象、漂浮凄美的情感、丰富大胆的想象和延伸扩展的语义。
诗歌虽然高雅但绝不高傲,她需要更多心灵的关照,就像娇艳的花朵不拒绝阳光。同时,诗歌是值得亲近的,那些从诗人生命历程中提取的意象,总在向诗爱者热情招摇。如果说诗中的意象总是诗人生命情感中最隐秘部分物化的需要,那么,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中那些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诸如“我”、“你”、“桔树”、“桔花”、“落叶”、“夕阳”、“雪花”、“行囊”,无疑昭示着诗人生命历程中有过最生动的瞬间或者最最刻骨铭心的美丽。这种瞬间和美丽可以是一场似乎已经割舍掉却又藕断丝连的爱恋,可以是一段想忘记却又挥之不去的情感,还可以是孜孜以求却终而无果的执著……
正是这些富有代表性的意象,提醒诗爱者们打开自己的想象,借助诗人客观冷静的叙写,去触摸诗人美丽动人的故事抑或彷徨迷离的情思。比如“桔树”,应该是浪漫故事的见证;“桔花”,应该是一段残缺而令人孜孜以求的美好。于是,“我”留在“桔树”下关于“桔花”的故事就上演了:我心已许终不变的约定,不知道什么原因,成为破碎的浪漫的曾经,但那份纯真,特别摄人心魄。“就算错过了花开/而我留在桔树下的诗行/还在绽放着美丽(《我曾如此靠近你》)。”失落的灵魂,万般无奈,只好选择等待,等待破碎的浪漫能够有修复的一天,“一个不知道/走向什么地方的灵魂/还能够在多久/才能等到/桔花再次灿烂的季节(《突然,心疼的感觉》)”。于是,不管叶落秋去,还是夕阳残照,最好是雪花的舞姿,都成为“你在他乡的消息(《我像雕塑一样等待》)”。所以,“我”还要背负着“行囊”,去经历,即使到达未知的遥远,也心甘情愿,因为“所有的依靠都在夕阳里歌唱(《幽梦》)”。
由于审美解读的多元化,我不敢通过对这些意象的解读就妄下结论,说某一首诗是爱情诗,或者定义整个诗集就是抒写爱情的集子。这个结论就留着吧,留给诗集本身去澄清。但是,我敢说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彻头彻尾被一种凄美笼罩着。或者说,李逢忠先生试图从诗的审美方面对诗进行澄清。
有人说:“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审美是凄美的”。不错,从《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从古诗到新诗,洋溢着凄美之情的名篇举不胜举。广安诗人李逢忠先生的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其中众多诗篇展示的审美恰好跟这句话暗合。只需稍加品读,诗爱者们就会发现,诗集中那个“我”深深爱恋的“你”,跟“我”总是聚少离多,无论“我”如何表白“我会等候/在你经过的渡口”(《把心交给我》),无论“我”多么有责任和担当,即使“我”“从来没有停止/对你的仰望”(《你就在我身旁》),但“你”留给“我”的总是离愁和思念。虽然这种情形多少有些凄凉,但“我”似乎并不厌弃,“我”总是在不停地怀念,找寻,“我问过风/风说:你在摇曳的花朵里/我问过雨/雨说:你在巴山/不灭的红烛里”(《想你的夜难以入眠》)。就在这样的凄美中,“我”享受着离情别绪,享受着别后的孤独。正是这种多情的孤独,诗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感空间,才有了梳理情愁的审美冲动。虽然理智战胜情感的时候,诗人会理性地觉得:最纯真的爱,绝不是一定要真正拥有;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是一种最美好的人生夙愿,所以,“我还是会在桔园/种下一个心愿/让那雨/穿越巴山深处的迷蒙/滋润着你”(《我用泪水浇灌你的幸福》)。
凄美不同于悲剧,可以让人悲而不伤、哀而不怨,属阴柔婉约的美。“就算是文字/还闪动着泪光/也要在心里升起朝阳”(《心愿》),真正的心不死而梦依旧,“只要还有一片落叶/梦就会在不远的地方/托起彩霞”(《黑夜的穿越》)。恰是这种细腻情感的柔美穿透,诗爱者会于自觉的情感交流中被柔化;在凄凉的包围下,一种深沉的执著跃上诗爱者心头。于是,诗爱者彻底幸福地淹没在诗的凄美中,享受着曾经属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审美绝唱。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不容争辩地用一首首纯情而凄美的诗篇澄清着一个永不褪色的事实:凄美也是新诗的。
如果说情感和理智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主宰,那么诗歌一定是情感冲破理智藩篱的产物。对于诗的创作者而言,在诗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情感始终是至上的。情感越活跃,想象越大胆,诗中的事实变得就越违反常理,变得甚至不合逻辑。于是,诗人仿佛变成了疯子,大凡世间一切的不可能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都那么浪漫而意趣盎然,竟连“那一朵花/落了又开了/似乎把春天的色彩/涂满了秋天”(《期盼》)。除了这种违反常理的诗歌事实,还有更多病态十足的诗句,也是情感疯狂到某种程度才催生的产物。“可我浅浅的期盼/还在摇曳”(《期盼》),“花/已没了昔日的芳香/碾作泥的/只是一瓣心事,一瓣凄伤”(《独坐敬亭山》):都是些跟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相悖的诗句。不过,我却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对诗歌语言的这种几乎病态的搭配有过多非议。相反,新诗的这种诗歌事实和诗歌语言正是其有别于大白话的特质所在,而新诗的诗味就在其中。这一点,也是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努力为新诗澄清的证据所在。
“你如薄雾般/轻盈的脚步/把露珠的梦踩碎”、“那些流浪已久的思绪/衔着太阳/在指尖升起”(《把太阳托在手上》)。在这样的浅唱低吟中,我们仿佛听到诗集《我在冬的尽头等你》时时吐露着一种为新诗澄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