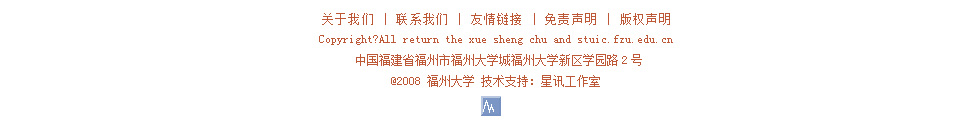雨天杂写之一
报载希特勒要法国献出拿翁当年侵俄时的一切文件。在此欧非两战场烽火告急的时候,这一个插科式的消息,别人读了作何感想,自不必悬猜,而在我看来,这倒是短短一篇杂文的资料。大凡一个人忽然想到要读一些特别的东西,或对于某些东西忽然厌恶,其动机有时虽颇复杂,有时实在也单纯得可笑。譬如阿Q,自己知道他那牛山濯濯的癞痢头是一桩缺陷,因而不愿被人提起,由讳瘌痢,遂讳“亮”,复由讳“亮”,连人家说到保险灯时,他也要生气。幸而阿Q不过是阿Q,否则,他大概要禁止人家用保险灯,或甚至要使人世间没有“亮”罢?倘据此以类推,则希特勒之攫取拿翁侵俄文件,大概是失败的预感已颇浓烈,故厌闻历史上这一幕“英雄失败”的旧事,因厌闻,故遂要并此文件而消灭之——虽则他拿了那些文件以后的第二动作尚无“报导”,但不愿这些文件留在他所奴役的法国人手中,却是现在已经由他自己宣告了的。
但是希特勒今天有权力勒令法国交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却没有方法把这个历史从法国人记忆中抹去。爱自由的法兰西人还是要把这个历史的教训反复记诵而得出了希特勒终必失败的结论的。不能禁止人家思索,不能消灭人家的记忆,又不能使人必这样想而不那样想,这原是千古专制君王的大不如意事;希特勒的刀锯虽利,戈培尔之辈的麻醉欺骗造谣污蔑的功夫虽复出神入化,然而在这一点上,暂时还未能称心如意。
我不知轴心国家及受其奴役的欧洲各国的报纸上,是否也刊出了这一段新闻,如果也有,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正如在去年希特勒侵苏之初,倘若贝当之类恭恭敬敬献上了拿翁的文件,便将成为堪付史馆纪录的妙事。如果真那么干了,那我倒觉得贝当还有百分之一可取,但贝当之类终于是贝当,故必待希特勒自己去要去。
雨天杂写之一历史上有一些人,每每喜以前代的大人物自喻。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野心家亚历山大,后来凯撒就一心要比他。而拿破仑呢,又思步武凯撒的遗规。从拿翁手里掉下来的马鞭子,实在早已朽腐不堪,可是还有一个蹩脚的学画不成的希特勒,硬要再演一次命定的悲喜剧。亚历山大的雄图,到凯撒手里已经缩小,但若谓亚历山大的射手曾经将古希腊的文化带给了当时欧亚非的半开化部落,则凯撒的骁骑至少也曾使不列颠岛上的野蛮人沐浴了古罗马文化的荣光。便是那位又把凯撒的雄图缩小了的拿翁罢,他的个人野心是被莫斯科的大火,欧俄的冰雪,烧的烧光,冻的冻僵了,虽然和亚历山大、凯撒相比,他十足是个失败的英雄,但是他的禁卫军又何尝不将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法兰西大革命的理想,带给了当时尚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欧洲人民?“拿破仑的风暴”固然有破坏性,然而,若论历史上的功罪,则当时欧洲的自中世纪传来的封建大垃圾堆,不也亏有这“拿破仑的风暴”而被摧毁荡涤了么?即以拿翁个人的作为而言,他的《拿破仑法典》成为后来欧陆“民法”的基础,他在侵俄行程中还留心着巴黎的文化活动,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然而即在此短暂的时间,他也曾奠定了法兰西戏院的始基,这一个戏院的规模又成为欧陆其他戏院的范本。拿破仑以“共和国”的炮兵队长起家,而以帝制告终,他这一生,我们并不赞许,——不,宁以为他这一生足使后来的神奸巨猾知所炯戒,然而我们也不能抹煞他的失败了的雄图,曾在欧洲历史上起了前进的作用;无论他主观企图如何,客观上他没有使历史的车轮倒退,而且是推它前进一步。拿破仑是失败了,但不失为一个英雄!
从这上头看来,希特勒连拿翁脚底的泥也不如。希特勒的失败是注定了的,然而他的不是英雄,也已经注定。他的装甲师团,横扫了欧洲十四国,然而他带给欧洲人民的,是什么?是中世纪的黑暗,是瘟疫性的破坏,是梅毒一般的道德堕落!他的猪爪践踏了苏维埃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花园,他所得的是什么?是日耳曼人千万的白骨与更多的孤儿寡妇!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而他的根本不配成为“失败的英雄”不也是已经注定了么?而现在,他又要法国献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如果拿翁地下有知,一定要以杖叩其胫曰:“这小子太混帐了!” [FS:PAGE]
前些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游览了兴安的秦堤。这一个二千年前的工程,在今日看来,似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二千年前,有这样的创意(把南北分流的二条水在发源处沟通起来),已属不凡,而终能成功,尤为不易。朋友说四川的都江堰,比这伟大得多,成都平原赖此而富庶,而都江堰也是秦朝的工程。秦朝去我们太久远了,读历史也不怎么明了,然而这一点水利工程却令我“发思古之幽情”。秦始与汉武并称,而今褒汉武而贬秦始,这已是听烂了的老调,但是平心论之,秦始皇未尝不替中华民族做了几桩不朽的大事,而秦堤与都江堰尚属其中的小之又小者耳!且不说“同文书”为一件大事,即以典章法制而言,汉亦不能不“因”秦制。焚书坑儒之说,实际如何,难以究诘,但博士官保存且研究战国各派学术思想,却也是事实。秦始与汉武同样施行了一种文化思想的统制政策,秦之博士官虽已非复战国时代公开讲学如齐稷下之故事,但各派学术却一视同仁,可以在“中央的研究机关”中得一苟延喘息的机会。汉武却连这一点机会也不给了,而且定儒家为一尊,根本就不许人家另有所研究。从这一点说来,我虽不喜李斯,却尤其憎恶董仲舒!李斯尚不失为一懂得时代趋向的法家,董仲舒却是一个儒冠儒服的方士!然而“东门黄犬”,学李斯的人是没有了,想学董仲舒的,却至今不绝,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我有个未成熟的意见,以为秦始和汉武之世,中国社会经济都具备了前进一步、开展一个新纪元的条件,然而都被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坏;不过前者尚属无意,后者却是有计划的。秦在战国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统一了天下,故分土制之取消,实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向,然而秦以西北一民族而征服了诸夏与荆楚,为子孙万世之业计,却采取了“大秦主义”的民族政策,把六国的“富豪”迁徙到关内,就为的要巩固“中央”的经济基础,但是同时可就把各地的经济中心破坏了。结果,六国之后,仍可利用农民起义而共覆秦廷,而在战国末期颇见发展的商业资本势力却受了摧残。秦始皇并未采取什么抑制商人的行动,但客观上他还是破坏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的。
汉朝一开始就厉行“商贾之禁”。但是“太平”日子久了,商业资本还是要抬头的。到了武帝的时候,盐铁大贾居然拥有原料、生产工具与运输工具,俨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雏形。当时封建贵族感到的威胁之严重,自不难想象。只看当时那些诸王列侯,在“豪侈”上据说尚相形见绌,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平准”、“均输”制度,虽对老百姓并无好处,对于商人阶级实为一种压迫,盐铁国营政策更动摇了商人阶级中的巨头。及至“算缗钱”,一时商人破产者数十万户,蓬蓬勃勃的商业资本势力遂一蹶而不振。这时候,董仲舒的孔门哲学也“创造”完成,奠定了“思想”一尊的局面。
所以,从历史的进程看来,秦皇与汉武之优劣,正亦未可作皮相之论罢?但这,只是论及历史上的功过。如在今世,则秦始和汉武那一套,同样不是我们所需要,正如拿破仑虽较希特勒为英雄,而拿破仑的鬼魂却永远不能复活了。
1942年6月27日桂林。
雨天杂写之二
佛法始来东土,排场实在相当热闹。公元三五○年到四五○年这不算短的时期中,南北朝野对于西来的或本土的高僧,其钦仰之热忱,我们在今天读了那些记载,还是活灵活现。石虎自谓“生自北鄙,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他对于佛图澄的敬礼,比稗官小说家所铺张的什么“国师”的待遇,都隆重些;他定了“仪注”: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我们试闭目一想,这排场何等阔绰!
其后,那些“生自北鄙,忝当期运,君临诸夏”的国主,什九是有力的护法。乃至定为国教,一道度牒在手,便列为特殊阶级。佛教之盛,非但空前,抑且绝后。然而那时候,真正潜心内典的和尚却并不怎样自由。翻译了三百多卷经论的鸠摩罗什就是个不自由的和尚。他本来好好地住在龟兹国潜研佛法,苻坚闻知了他的大名,便派骁骑将军吕光带兵打龟兹国,“请”他进关。龟兹兵败,国王被杀,鸠摩罗什做了尊贵的俘虏,那位吕将军异想天开,强要以龟兹王女给鸠摩罗什做老婆。这位青年的和尚苦苦求免。吕光说:“你的操守,并不比你的父亲高,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原来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本为天竺贵族,弃嗣相位而到龟兹,极为那时的龟兹国王所尊重,逼以妹嫁之乃生鸠摩罗什,所以吕光说了这样的话,还将鸠摩罗什灌醉,与龟兹王女同闭禁于一室,这样,这个青年和尚遂破了戒。后来到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为国王姚兴所敬重,姚兴对他说:“大师聪明,海内无双,怎么可以不传种呢?”就强逼他纳宫女。这位“如好绵”的大师于是又一次堕入欲障。这以后,他就索性不住僧房,另打公馆,跟俗家人一样了。这在他是不得已,然而一些酒肉和尚就以他为借口,也纷纷畜养外室;据说鸠摩罗什曾因此略施吞针的小技,警戒那些酒肉和尚说:“你们如果能够象我一样把铁针吞食,就可以讨老婆。”每逢说法,鸠摩罗什必先用比喻开场道:“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不用理那臭泥。”即此也可见他破戒以后内心的苦闷了。姚兴这种礼贤的作风,使得佛陀耶舍闻而生畏。耶舍是罗什的师,罗什说姚兴迎他来,耶舍对使者说:“既然来请我,本应马上就去,但如果要用招待鸠摩罗什的样子来招待我,那我不敢从命。”后来还是姚兴答应了决不勉强,佛陀耶舍方到长安。 [FS:PAGE]
但是姚兴这位大护法,还做了一件令人万分惊愕的事。这事在他逼鸠摩罗什畜室之后五六年。那时有两个中国和尚道恒道标被姚兴看中,认为他们“神气俊朗,有经国之量”,命尚书令姚显强逼这两个和尚还俗做官。两个和尚苦苦求免,上表陈情,举出了三个理由:一,他们二人“少习戒法,不闲世事,徒发非常之举,终无殊异之功,虽有技能之名,而无益时之用”;二,汉光武尚能体谅严子陵的志向,魏文亦能顾全管宁的操守,所以圣天子在上,倒并不需要大家都去捧场;三,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他们两个一心一意做和尚,正是从别一方面来拥护姚兴,帮他治国,所以不肯做官并非有了不臣之心。然而姚兴不许,他还教鸠摩罗什和其他的有名大师去劝道恒道标。鸠摩罗什等要替道恒道标说话求免,说“只要对陛下有利,让他们披了袈裟也还不是一样?”但是姚兴仍不许,再三再四叫人去催逼,弄得全国骚然,大家都来营救,这才勉勉强强把两领袈裟保了下来。道恒道标在长安也不能住了,逃避荒山,后来就死在山里。
这些故事,发生在“大法之隆,于兹为盛”的时代,佛教虽盛极一时,真能潜心内典的和尚却有许多不自由。而且做不做和尚,也没有自由。但姚兴这位护法还算是有始有终的。到了后魏,起初是归宗佛法,敬重沙门,忽而又尊崇道教,严禁佛教,甚至下诏“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悉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但不久复兴佛教,明诏屡降,做得非常热闹。当此时也,“出家人”真也为难极了。黄冠缁衣大概只好各备一套,看“早晚市价不同”随机应变了。
1942年7月25日桂林。
雨天杂写之三
不知不觉,在桂林已经住了三个月。什么也没有学得,什么也没有做得,就只看到听到些;然亦正因尚有见闻,有时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来有半月多,不拉警报了,这是上次击落敌机八架的结果;但也有近十天的阴雨,虽不怎么热,却很潮湿,大似江南梅雨季节。斗室中霉气蒸郁,实在不美,但我仍觉得这个上海人所谓“灶披间”很有意思;别的且不说,有“两部鼓吹”“两部鼓吹”:当时,我住的小房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胜况空前(就我个人的经验言)。而“立部”之中,有淮扬之乐,有湘沅之乐,亦有八桂之乐,伴奏以锅桶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国气派。内容自极猥琐,然有一基调焉,曰:“钱”。
晚上呢,大体上是宁静的。但是我自己太不行了,强光植物油灯,吸油如鲸,发热如锅炉,引蚊成阵,然而土纸印新五号字,贱目视之,尚如读天书。于是索性开倒车,废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强光植物油灯,而复古于油盏。九时就寝,昧爽即兴,实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梦回,木屐清脆之声,一记记都入耳刺脑,于是又要闹失眠;这时候,帐外饕蚊严阵以待,如何敢冒昧?只好贴然僵卧,静待倦极,再寻旧梦了。不过人定总可以胜“天”,油灯之下,可读木板大字线装书;此公此公:陈此生同志也。为我借得《广西通志》,功德当真不小。
而且我又借此领悟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说来贻笑大方,盖即明白了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啸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 [FS:PAGE]
三星期前,忽奋雄图,拟游阳朔;同游十余侣,也“组织”好了,但诸君子皆非如我之闲散,故归途必须乘车,以省时间。先是曾由宾公设法借木炭车,迨行期既迫,宾公忽病,脉搏每分钟百八十至,于是壮游遂无期延缓。但阳朔佳处何在呢?据云:“阳朔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析成天柱者数十里,如楼通天,如阙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马啮,如阵将合,如战将溃,漓江荔水,捆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态”(《广西通志》),这里描写的是山形,这样的山,当然无可登临,即登临亦无多留恋,所以好处还是在洞;至于阳朔诸峰之洞,则就不是几句话所可说完的了。记一洞的一篇文章,往往千数百言,而有些我尚觉其说得不大具体呢!
还有些零碎的有趣的记载:太真故里据说在容县新塘里羊皮村,有杨妃井,“井水冷冽,饮之美姿容”。而博白县西绿萝村又有绿珠井,“其乡饮是水,多生美女,异时乡父老有识者,聚而谋窒是井,后生女乃不甚美,或美矣必形不具”。然而尤其有意思的,乃是历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在《广西通志》内有一段未定的消息,全文如下:“横州寿佛寺,即应天禅寺,宋绍兴中建,元明继修之。相传,建文遇革除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余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受浮屠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
建文下落,为历史疑案之一,类如上述之“传说”颇多,大抵皆反映了当时“臣民”对于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猜疑好杀,忆杂书曾载一事,谓建文进言,以为诛戮过甚,有伤和气。异日,太祖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难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复令建文拾之,既乃诏之曰:“我所诛戮,皆犹杖上之刺也,将以贻汝一易恃之杖耳?”这一故事,也描写到建文之仁厚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却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诸王子中。
明末最后一个小朝廷乃在广西,故广西死难之忠臣亦不少;这些前朝的孤忠,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皆蒙“恩”与死于“流贼”诸臣,同受“赐谥”之褒奖。清朝的怀柔政策,可谓到家极了。
说到这里,似乎又触及文化什么的了,那就顺笔写一点这里的文化市场。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当抹煞。有一位书业中人曾因作家们之要赶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费之议那时候,排字工人排一千字的工资高于作家一千字所得的稿酬,故作家有“赶上排工”之议。,遂慨然曰:“现在什么生意都比书业赚钱又多又稳又快,若非为了文化,我们谁也不来干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们现在之斤斤于稿费,毋乃太不“为了文化”。这位书业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里真相如何,这里不想讨论,无论主观企图如何,但对文化“有功”,则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个文化市场支撑起来了,而且弄得颇为热闹。
然而,正如我们不但抗战,还要建国,而且要抗建同时进行一样,我们对于文化市场,亦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书出,我们还须看所出的书质量怎样,还须看看所出之书是否仅仅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抑或同时亦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举个浅近的例,目前大后方对于神仙剑侠色情的文学还有大量的需要,但这是读者的需要,可不是我们文化发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这两个需要比较起来,我们就不能太乐观,不能太自我陶醉于目前的热闹,我们还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FS:PAGE] 大凡有书出版,而书也颇多读者,不一定就可以说,我们有了文化运动。必须这些出版的东西,有计划,有分量,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文化市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对文化运动无大贡献,我们只建立了一个文化市场。这样一桩事业,照理,负大部责任者,应是所谓“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颇多的中国,出版家在这上头,时时能起作用,过去实例颇多,兹可不赘。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话,决非单独对出版家——宁可说主要是对我们文化人自己,但也决不想把出版家开卸在外,因为一个文化市场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无出版家,进一步,又不能说与读者无关。
我想用八个字来形容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这八个字不大好看,但我决不想骂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无非想把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加以形象化而已,这八个字便是:“鸡零狗碎,酒囊饭桶!”
这应当有一点说明。
前些时候,此间书业公会开会,据闻曾有提案,拟对抄袭他家出版品而成书的行为,筹一对策,结果如何,我不知道。说到剪刀浆糊政策在书业中之抬头,似乎由来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场上,据说已经相当令人头痛,目前有几本销路不坏的书,都是剪刀浆糊之结果。剪刀浆糊不生眼睛,于是乎内容之庞杂芜秽,自属难免。尤其异想天开的,竟有抄取鲁迅著作中若干段,裒为一册,而别题名为《鲁迅自述》以出版者。这些剪来的东西,相应不付稿费版税,所以获利尤厚,据说除已出版者外,尚有大批存货,将次第问世。当作家要求增加版税发议之时,就有一位书业中人慨然认为此举将助长了剪刀政策。这自然又是作品涨价毋乃“太不为了文化”同样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却已暗示了剪刀之将更盛。呜呼,在剪刀之下,一部书将被依分类语录体而拆散,而分属于数本名目不同之书中;文章遭受了凌迟极刑,又复零碎拆卖,这表示了文化市场的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这样的办法,既非犯法,自难称之曰鸡鸣狗盗,倒是这样的书倘出多了,若干年以后也许会有另一批人按照从《永乐大典》中辑书之例,又从而辑还之,造成一“新兴事业”,岂不思之令人啼笑皆非么?但书本遭受凌迟极刑之现象既已发生,而且有预言将更发展,则此一特点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拟题曰“鸡零狗碎”云尔。
其次,目前此间文化市场除了作家抱怨出版家只顾自己腰缠不顾作家肚饿,而出版家反唇相讥谓作家“太不为了文化”而外,似乎都相安无事,皆大欢喜。文化市场被支撑着,热热闹闹,正如各酒馆之门多书业中人一样热闹。热闹之中,当然亦出了若干有意义的好书,此亦不容抹煞,应当大书特书。不过,这种热闹空气,的确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这大概也可算是一个特点。无以每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来者,七十个出版家名月还出相当多的书,当然也解决了直接间接不少人的生活问题,无怪在作家要求维持版税旧率时,有一先生曾经以“科学”方法证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书到明天便只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价天天在涨,法币购买力天天在缩小。由此所得结论,作家倘不减低要求,让出版家多得利润,则出版家经济力日削之后,作家的书也将不能再出,那时作家也许比现在还要饿肚子些罢?这笔账,我是不会算的,因为我还没干过出版,特揭于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值得专家们讨论。不过可喜者,现在还不怎样严重,新书店尚续有开张,新书尚屡有出版,这大概不能不说是出版家们维持之功罢?文化市场既然还撑住,直接间接赖以生活者自属不少;而作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近来还没有听见说作家中发现了若干饿殍,而要“文协”之类来布施棺材,光这一点,似乎已经值得大书特书了罢?用一不雅的名儿,便是“饭桶”,这一个文化市场,无论其如何,“大饭桶”的作用究竟是起了的。于是而成一联: [FS:PAGE]
饭桶酒囊亦功德,
鸡鸣狗盗是雄才。
1942年6月30日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