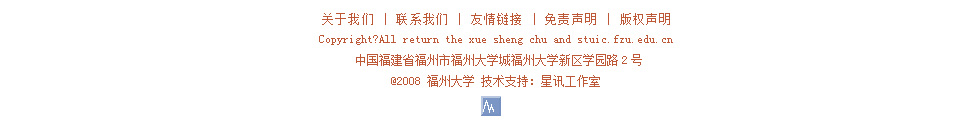北大的董学文先生是我的私慕恩师,或者好听一点说,我是他的私淑弟子,其实如果再准确些说,我只是他挂单的编外弟子。因为我既不是北大出身,做访问学者,校方也没有指定他是我导师。和董先生的交往,完全是巧合,或者说是靠缘分。 我去北大访学,由于没有选课的任务,想听谁的课就听谁的课,出于专业兴趣,我听了董先生为博士生开的“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讨论课,这是我有幸拜董先生为师的主要契机。 由于“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是以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理层次较高、抽象度较大的引领性讨论课,所以,很快,慕名而来的许多访问学者,进修教师以及硕士生们就因自己学养、专业兴趣等方面的差距纷纷退场了。由于我一直对这个领域有兴趣,而且在先生的有效启发、引领下,学科思想开始逐渐入轨,因此,我就成为该课为数不多的聆听者与参与者之一。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在听课人中稍大,而且又与先生是同乡,所以很快就在课堂讨论中经常被先生指定为主要发言者。我一边深深地为先生的博学所折服,为其思想的深刻、见地的独绝所打动,另一方面,由于先生平易的学风,仁厚的长者气度的鼓励,开始发表自己对有关理论问题的困惑、设想。令我感佩的是,即便是我的困惑很浅薄,设想很幼稚,先生不仅注意听,而且总是在耐心的解答中,选取我发言中哪怕只是些微的闪光点给予充分肯定,甚至高度评价。这对一个蹭听、而且是来自边远小学校的访问学者,实在是难以想象的鼓励。于是,我开始大胆表述我的想法,自然,受到的鼓励也较多。有一次,在一个问题上,我与先生的观点相左,于是发生了思想的撞击。先生的一位博士生出于好心,为缓冲这种撞击的强度,在发言中有意误读我的话,这使先生大为恼火,当即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曲解,并告诫这位亲门弟子,在学术讨论上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人人平等,在这里,只有真理才是至高无上的。先生博大的学术胸怀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使在场者身受感动,于是,讨论更加热烈而有效。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什么叫有大乃容,什么是北大精神。 由于关系越来越熟、感情越来越近,我就把我的一些学术习作请先生指导。先生每次都象给小学生批作业一样认真审阅,有时,一稿竟看五六遍之后,才给我明确的指示。本来,先生作为名流学者、学界前排人士,社会、学术兼职极多,诸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还是若干综合性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答辩委员会主任,等等,每天有应接不暇的邀请、求教和稿约,能对我这学术上很不成熟的编外弟子如此垂青关爱,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有的稿件,先生常常为我改了又改,叫我重写数次,直到他满意为止。而且,先生虽然从不介意我由于性格方面的缺点偶尔对先生有所不恭和冒犯,却不能容忍我在做学问上有一丝一毫的投机取巧。譬如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避重就轻地谈问题,先生不由大怒,责令我重写,并告诫我,一个观点要立得住,就必须和最不利于你的思想较量,这样才有价值,才是学术的有效积累。先生的话,虽然当时使我羞愧不已,但在心底里,却十分感激先生无私严正的教诲。 先生总是想方设法为弟子们提供锻炼、发展的机会,对于我每一篇他认为过关的文章,先生都竭力推荐,力争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次全国综合性大学文学原理教材研讨会上,先生郑重委托我代表北大做主要发言,这对一个不见经传的编外弟子,实在是不敢想象的殊荣。 先生虽然对包括象我一类的弟子关怀备至,但从来不允许弟子们对他有任何孝敬的表示,哪怕是课间休息时,有的学生为他买一瓶矿泉水,先生也要一定付钱。放假期间,有时从家返校,出于礼貌,为先生带点地方特产,先生不好推拒,就再给我带回一些别的东西,从商品价值讲,一定是超过我的多少倍。 听其别人讲,先生曾有多次出仕为官的机会,甚至是副部级的高位,但先生以学术为业,都一一婉拒,至今,正式官职仅是教研室主任。这在盛行跑官、买官的当今社会,这种对学术的坚守和对专业的痴情,实在令人叹为闻止。 在学术追求上,先生从来不追风、不赶潮,但决不保守,而是以深厚的学养、宽容的心态和质疑的目光融化各种前卫学说,辨析、吸纳其真理性因素,作为构建自己学术思想的新质和产生卓见的诱因,决不简单拿来,也不粗暴拒斥。所以,在我看来,先生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他一直足踏中西两界,俯视各色理论,自成一家之言。 得拜先生为师,实在是前世结的善缘,否则,我何以如此幸运?象先生这样居高不矜,渊博不显的大学者风范,在当下日见浮躁而势利的学界已为稀世之珍。和我一样的访问学者,有的虽有校方指定的导师,但整整一年,没有得到过导师一字一句的指点。所以如此,恐怕不仅仅是师生学养之间的差距吧? 所以,作为身受大恩的弟子,对先生唯一的报答,就是多做出一些成绩来,道一声,谢谢、恩师。 文章来源:中国散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