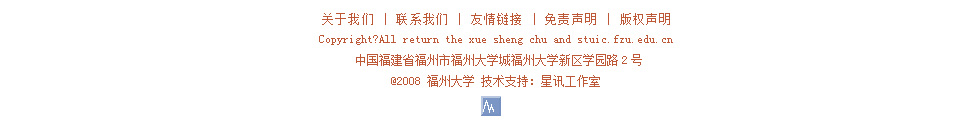人们常把“礼”与“俗”合起来称“礼俗”,可见礼与俗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历代许多经学大师在给《仪礼》《周礼》《礼记》等作注作疏时,常常将礼与俗混为一谈。例如关于“礼俗丧纪祭礼皆以地媺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郑玄注曰:“礼俗,邦国都鄙民之所行先王旧礼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随其土地厚薄为之制丰省之节耳。”贾公彦疏:“俗者,续也。续代不易,是知先王旧礼,故引《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以证之。谓若周公封康叔于殷墟,其民还行殷之礼俗者也。”这里郑注与贾疏都将礼与俗混用。
事实上,俗不等于礼,但是有些风俗经过一定的整理加工便可上升为礼,有些礼本身则是起源于民间风俗的。在远古时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就有了自己的风俗,这些民间的风俗,有些上升为民间的礼节,若能在相当范围内受到大众赞许并得以普遍遵循,具备了礼的要素,就成为民间的礼制。反之,某些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朝代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取舍不同,已经不为官方所推行,只在民间世代相传,形成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而保存下来,虽几经改易面目有所不同,但仍依稀可见远古时代相关礼仪的影子。《仪礼》所记载的诸种生活礼仪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极深远的,这从古代所流传的风俗习惯即可略见一斑。例如“士冠礼”对民间流行的“成年礼”,“丧服”“士丧礼”对民间丧葬习俗,“士昏礼”对民间婚嫁习俗,“馈食礼”对民间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乡饮酒礼”对敬老养老风俗、饮食文化、宴饮之礼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风民俗虽不是社会意识的系统形态,但在普遍的下层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精神,表现了传统教化的特色。
每个人一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具有了社会性。他无时无刻不在接触和熟悉他所生活的社会,吸收这个社会经过长期积累存留下来的各种知识,受到社会各种风俗习惯礼仪的潜移默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作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而在种种社会风俗习惯中,成年礼是对一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礼俗之一。它在精神上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形式所带来的效果。
《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祭丧,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对其成员的成年都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其意义不仅是自身心理、生理的成熟,而更在于这是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亚于生命的诞生。即使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都有正规的成年礼。《仪礼》中所记载的“冠礼”正是这种成年礼的遗留,后来经过统治者的加工改造,从而具有了更完备的仪式过程。虽然它后来已不作为一种制度被推行,但它已经成为风俗习惯而被保存下来。它虽然主要是流行于贵族士人阶层,但在许多所谓的衣冠诗礼之乡,一般百姓人家也有举行这种成年礼的。在中国各地风俗志中有许多关于成年礼的记载,不胜枚举。民间所流行的冠礼,与古制有所不同:首先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提前了,大多是在十六岁的时候。这可能与民间婚龄提前有关。再者,冠礼的仪式简化了不少,不再如以前繁琐,例如嘉靖《宁波府志》记宁波士农商贾所行冠礼,“一从简朴,仅取成礼”。民间的冠礼往往与婚礼联系在一起,只有成年人才可以结婚,因此,又有赶在婚礼之前举行冠礼的。冠礼在不同地区流行,往往会带上各自的民俗色彩。例如《至元嘉禾志》记元代时桐乡一带风俗云:“男子十六始冠,亦有婚而冠者。女子于归乃笄,聚族张筵。凡冠笄,皆炊大糕,馈遗亲里,始讳其名而字之。”很明显地带有了欢乐的喜庆色彩。
民间流行的成年礼虽然在形式上与《仪礼》所记载的古制有很大区别,但基本上还是它的延续,在精神上还是一贯的。成年礼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成熟,而且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原先的儿童作为成年人的新的资格的认可。“这种授予新的地位又委以新的义务的仪式就像地位和义务本身一样各有千秋且受着文化的制约。”(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在中国,成年礼所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而,我们对成年的要求就明显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要求。随着“以成人见”的礼仪之后的是“责成人之道”的要求。唐代柳宗元在《与韦中立书》中云:“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冠也。”《国语》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赵文子行冠礼之后,去见韩献子,献子告诫他说:人行了冠礼,就是成人了,就像宫室有了墙屋,不能只求洁身自好,还要担当驱除不善的责任。所谓的“成人之道”就是指成年人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与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家里要尽孝悌的义务,在社会上承担起为子民人臣的责任。
继成年礼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礼仪便是婚礼。《仪礼·士昏礼》所记载的著名的“六礼”的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对民间婚礼仪式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仪式程序。“六礼”在后世于程序上逐渐简化,内容也几经变革。例如,纳采、问名、纳吉诸礼合并为纳采,单方面的问名改为双方交换写明男女姓名、出生年月日时(即俗称的“生辰八字”)和父祖三代姓名官衔的庚帖(即俗称“龙凤全帖”)的订婚仪式。此时,男家致送订婚礼物,俗称“放小定”,用雁是不可能的了,有些地方以鹅代替,但茶是一定要的,因而也有称“下茶”的。而纳征与请期也往往合并,俗称“下聘”,也称“放大定”,是正式的聘礼,一般依各自的门第、财力而决定聘礼的丰俭,大体包括首饰衣物食品等物。亲迎的程序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不过时间改在白天,用花轿代替了“御轮”。这些程序,一旦成为风俗,往往不会轻易改变,否则容易招致乡里的非议。这也体现了中国人守“礼”的文化根源。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老病死是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事,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古人往往极看重葬礼,它不仅是对死者身份、地位的确认,而且是儒文化中“孝”的重要体现方式。民间的丧礼及丧服制度基本上仍保留了远古时代的礼仪。从属纩、行复礼,沐浴,入殓、饭含到殡、出殡,及出殡时的执绋、唱挽歌都被不同程度地沿袭下来。其中,执绋和唱挽歌比较多地吸收了世俗的成分,它带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和随意性,也体现了礼和俗的交流。挽歌在周代,只是一种民俗事象,而未入礼;到汉代,它成为上层社会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到南北朝时更为流行。由俗入礼,又由礼到俗,其中双方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统丧服制度自《仪礼》中规定之后,直到民国政府的《北泉礼仪录》,固然时有变通更革,但基本上是沿袭不衰,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次,即“五服”。古代社会里,丧服制度适用于自天子到平民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民间除了“五服”之外,还有一种免祖服,更轻一些,是包括同宗同姓的一类。随着历史的演变,服丧习俗也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整个社会丧服服饰习俗往往会随着新的质料的出现、崇尚观念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宋代《书仪》云:“大功、小功、缌麻皆用生白绢为襕衫、系黑鞓角带,大功以生白绢为四脚。妇人以生白绢为背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绢为头盖头,小功缌麻勿着华采之服而已。”这里很明显地带有了宋代服饰的特色。其他如服丧对象、人员及服丧期等方面,各个朝代不同地区也常有所不同。
有丧必有祭,祭祖礼与丧礼一样,自《仪礼》以来沿袭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表现为鬼神信仰,或表现为祖先崇拜。我们从《仪礼》及《礼记》中可以看出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祖先信仰体系。对祖先的崇拜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特征。孔子虽从不谈论鬼神之事:“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对祭祀祖先却十分重视,说自己是殷人之后,从小即学习祭祖礼。民俗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方式仍是祭祀,包括立宗庙、祖宗祠堂及一系列祭祖礼仪。这种祭祖礼非常复杂,名目繁多。有“家祭”“节祭”“村祭”“族祭”等。“家祭”所祭祀的对象通常是到祖父母、父母为止,主要是在先人的生日、忌日时祭祀,仪式相对简单。“节祭”是“家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象仍以祖父母、父母为主,但范围又可扩大到曾祖高祖,一般是在清明节、中元节、送寒衣节、冬至、除夕等节令举行祭祀活动。至于“村祭”“族祭”的范围则更广了,祭祀的对象上推到同一村寨或同一族成员的共同祖先,一般以祠堂为祭祀活动的场所。这种种仪式都是人们对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的维护和体现。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宗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的、最该供奉的祖先,因为整个社会的伦理是以“己身”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关系的。中国人或许对神、对宗教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但对祖先却是怀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混杂着自觉的敬仰与本能的折服和归依感。因此,中国民俗中,祭祖常常是最热闹的最隆重的活动。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看,祭祖是人们意识趋向、内心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反映,表现了人们对家族关系的崇尚。祭祖虽是祭死去的人,其实质仍是指向现世中的人,其精神是顺从和孝敬,是和睦亲好,是家族的前途和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崇拜是从维系家族、氏族甚至民族利益出发的一种对于祖先的追念,这种崇拜有利于调动家族之间、氏族之间乃至民族之间所有成员彼此和睦团结的情感和道德,这才是祖先崇拜的深刻内涵和意义。
中国民俗丰富多彩,但无不有其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仪礼》中所载的诸种礼仪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可谓极为深远。除了上述种种,民间崇尚的尊长敬老的风俗、宴饮礼节及饮食习俗、座次方位及尊卑等等,也都可以见到上古相关礼节的影子。(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