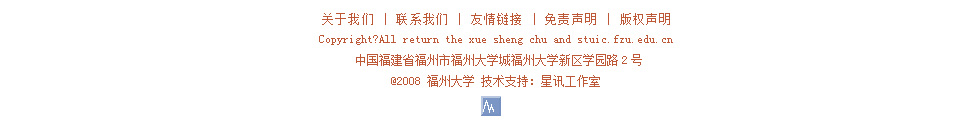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 任琳
编者按:对于美国“退出外交”的分析局限于既有理论流派的泾渭分明与特朗普个性外交的掩饰,因此很难准确理解“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影响和实质。本文试图从制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予以分析,寻求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借助权力与制度两种分析变量,进一步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制衡手段的“退出外交”。
本文提出“退出外交”也可被称为“退群外交”,用以概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治理多边建制层面做出的退出表态,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美自贸区等以退出或威胁退出为手段,借以实现一定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举措。一改往日高举自由主义秩序大旗的常态,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单边退出既有国际多边机制,做出了反建制的表态。统观美国“退出外交”涉及的内容、领域和组织形态乃至退出落实情况,可谓各有千秋。
通过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理解“退出外交”的发生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秩序的客观属性是导致权力在权力资源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出现转变的根源性诱因:有些表现为秩序在制度层面上的转变,有些表现为秩序在权力资源层面上的转变。作为制度转变的反应机制,退出同样是转变制度制衡方式的重要表现;作为针对权力转变的反应机制,退出也是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手段。面对权力离散,作为秩序主要维系者的既成大国美国做出应对方略,希冀于避免自身权力流失。当既成大国对这种权力流失的容忍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产生“退出外交”。
一、溢出效应与退出应对
制度的溢出效应描述的场景正如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带来不可控的系统性结果。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很容易导致权力从卖方向买方的分散,这意味着完全竞争市场的奠定者(一般是部分大公司)可能在竞争的初期享有规则制定者的“先行者优势”。但是随着竞争环境的自由化程度加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之间不断进行价格比拼和竞争,最终导致消费者在买方市场受益。同样,完全竞争市场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规则主导国设计制度的原初目的。
尽管存在诸多不同点,全球治理秩序依然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随着制度的普及、适用和被理解,某种国际体系或全球治理秩序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即建构主义所认为的把社会建构变量内化为对体系内成员的约束力不断增加的个体偏好,即使规则和制度的核心创设者和拥有国际领导权的国家,也不得不受到来自这套具备功能导向性规则、制度与规范的约束。制度具有维持贸易、金融、货币等领域内功能性交易的作用,正是制度的这种功能规范了行为体行为并塑造了系统内部秩序。
但是,正因为制度规则具有功能性导向,提供不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作为这套秩序起初建立基础的权力结构也被慢慢瓦解。构建之初,秩序领导国拥有的权力资源优势被慢慢稀释,进而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可能性随之下降。制度构筑了一定的约束性秩序,而作为制度主要“供应方”且处于主导地位的既成大国也无法挣脱,更无法避免权力向同样作为制度“消费方”的其他国家发生偏移。
制度体系一旦被创设出来,就具有独立性,“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这种制度创造的稳定秩序框架下,存在生产更多权力资源的可能,例如“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均势政府(权力均衡)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而这种论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现实主义主张的军事实力比拼不再是当今国际社会上唯一的权力博弈手段。
当然,权力博弈依然重要,但博弈内容已今非昔比。全球治理秩序的溢出效应为通过自由贸易创造财富,生产新的权力资源创造了可能。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析话语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融合了,并且孕育出一种独特的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元素。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话语下,主导国要利用“退出外交”减少源自溢出效应的权力流失,主要通过调整和影响多边治理机制的方式,进而制衡来自竞争对手的权力上升之势。溢出效应可以瓦解既成大国权力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相对自由竞争环境下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二是秩序体系内差异性下降,原盟国体系日趋出现务实导向。而针对这两个层面上权力流失而言的“退出外交”,算得上是一种即时的策略调整。
随着全球化进程日趋深入,各行为体深度复合相互依存,全球治理秩序的社会性不断增强与稳定,制度的溢出效应愈发明显。美国面临的世情由此逐渐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俱乐部实力却因向心力下降而相对衰弱,美国对溢出效应的容忍度不断趋近极限。
二、消耗效应与退出应对
人类社会得以稳定与进步,需要制度维系,其核心就是契约精神。在国际社会,契约精神说的是依照约定,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国际义务。契约的作用在于约束行为体行为,确保公共产品的筹集。运营一个大量需求公共产品的系统在客观上导致了权力资源的消耗。在霸权稳定论等相关理论论述中,霸权的衰落纯粹是因为霸权国无法支付维持制度治下秩序所需的高额治理成本。
特朗普借“退出外交”减少国际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回应权力资源层面上出现霸权衰落的举措。在这些理论话语中,国际制度是一个消耗霸权国力量的治理中介。虽有合理成分,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一方面,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秩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美国也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但另一方面,这种论述实则变相掩盖了作为这套制度设计者的霸权国家从中获得大量非中性利益的事实。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话语下,退出多边规则也反映出一种平衡权力竞争,或者说平衡潜在威胁的战略倾向。美国通过退出多边规则,减少自身开支,要求崛起国分摊成本,进而起到平衡威胁的作用。所以此类制度制衡的直接对象是消耗效应,对象国主要是挑战美国权力优势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一)通过退出减少制度约束,制衡制度消耗
就美国国内而言,尽管经济有所复苏,但增长依然相对缓慢,加之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美国想选择性地不再承担部分国际责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保持国际竞争优势。既然要抛掉一些包袱,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有意无意地想要制衡来自治理秩序的消耗效应,主要表现为摆脱制度约束,拒绝继续支付乃至转嫁部分治理成本。退出部分多边制度是特朗普强调本国利益的重要体现,是进行出于本国私利(降低制度消耗)而非全球公利(公共产品供应)的重置秩序之举。这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秩序的权力失衡、程序不民主、全球发展失调、公共产品赤字和全球治理失灵等现实问题与挑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后者考虑的是确保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特朗普思考的却是修复美国霸权的问题。
(二)“退出外交”的实质是通过转嫁成本,制衡竞争威胁
向处于竞争关系的对手国家转嫁日益上涨的全球治理成本,表现为一种新的制衡威胁的手段。通过“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制与拖欠联合国会费,特朗普希望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付出治理成本与提供公共产品。这种转嫁治理成本的行为同样是依照“美国优先”原则进行议题排序:一方面,美国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国际问题次之;另一方面,却要求其他国家分担全球治理成本,强调将重视国际义务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制度现实主义制度制衡的分析话语,虽与以往现实主义话语中的结盟和均势等传统的制衡手段有所差异,但依然具有权力博弈与竞争的色彩。特朗普所谓的“退出外交”期许通过制度制衡一方面减少自身付出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又达到通过转移治理成本,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战略遏制目标。“退出外交”的起点就在于既成秩序的功能属性消融了权力属性,降低了既成大国得自秩序的非中性收益。现实主义的分析话语恰恰是如此被引入到全球治理多边制度体系的分析之中。
(摘自《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