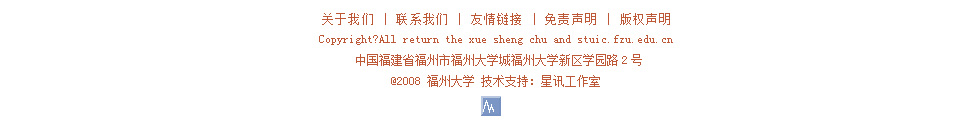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治必要性,已毋庸置疑。那么,从学理上来说,两者的结合能否立得住呢?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成立。理由是:
第一,以德治国不仅注重动机文明的建设,同时它也注重知行合一,关注“行为文明”的建设,这与法律着重于调整人们的行为特性,是相当吻合的。
以德治国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人的素质。从人的活动过程看,包含着“动机文明”和“行为文明”两个基本内容,而在这两个方面中,我们容易求得的是“行为文明”,而较难获得“动机文明”。因为“动机文明”既源于动机的内隐、复杂,也出于由此而来的不易梳理与表述。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外显的、可感知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有时却是隐蔽的甚至是极其隐秘的、不可感知的。相同的动机可以表现为迥然相异的行为,相同的行为也可以源自大相径庭的动机。而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通常都是诸多单向动机交互作用而成的融合物,显意识与潜意识交织、融合在一起,其纷纭复杂,甚至连行为者本人都难以言说清楚。此外,与具有社会公共生活意义的“行为”不同,“动机”纯属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情感活动,并无社会公共性。因而要求人的动机文明,是必要的,但却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还要防止“思想侦查”倾向。
所以,以德治国最终会落脚到“行为文明”的建设上,行为文明应是以德治国的生长点、出发点与纲领。抓住了它,以德治国的全局就可纲举目张,稳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顺理成章了。因为相对道德而言,法律主要调整人们的行为,它要求从外部遵守现有的规则。当然,它也不是绝对不考虑人的动机。犯意是定罪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之一,过错责任也是民法的重要原则。但法律决不搞“诛心”,主要是看行为。
法律同道德一样,都负有培育人们良好品质的使命,只不过两者的路数不一样。法律的路数是:通过管住人的行为,然后提高人的觉悟。而道德的路数是:通过教育、启发人们觉悟,然后端正人们的行为。两者异曲同功、殊途同归。
从实践来看,各地开展以德治国的做法一般都落脚到乡规民约、行规公约等具体行为文明建设上。
第二,以德治国的基点是建设“群体行为文明”,这与法律“稳定性、普遍性”的特点是相当吻合的。
中央一系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的文件多次表述一个观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讲先进性,思想道德教育就可能迷失方向。但不讲广泛性,思想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和社会文明的整体提高,就会成为问题。因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个人修身养性是社会成员的个体活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规模宏大的群体活动。这个区别看似十分明显,却往往被人们忽视。长期以来,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直在用对待个体活动的方法对待群体活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全部错误几乎都可归结为这一点),即把全社会参与其事的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了个人的修身养性之事。这一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着眼点放在培养个体典型上,以为几个先进个体的出现就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任务,或者说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培养若干先进个人即可完事;(2)在衡量、评估精神文明建设时,以先进个体的多寡为尺度,而不以社会整体风气的优劣为标准。
上述偏差的要害是忽视了群体活动与个体活动的差别。首先,个体的精神文明状况固然对群体精神文明状态有影响,但毕竟与后者是两回事。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乏极为优秀的文明个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优秀文明个体同时的社会群体的文明水平都很高,群体精神文明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先进个体的行为。其次,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在动力机制上有着重大差别。个体在其活动中既可能以经济利害关系为转移,也可能以人的超功利的信仰、道德、情感等精神性因素为转移,直至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群体活动则不然,群体在其活动中首先考虑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对信仰、道德、情感等因素采取何种态度,都最终取决于对经济利害关系的衡量与选择。
因此,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固然要树立一批批时代的英雄模范,重视文明个体的榜样示范作用,而且必须承认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同时必须以“群体行为文明”为基点。先进的个体固然多多益善,但与群体相比,他们总是少数和例外,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载体与主体,始终是群体;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心,始终是“群体行为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衡量尺度,始终是“社会风气”。
如果这一观点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法律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即:法律调整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法律从不特意为某人所设。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与普遍性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经常为哲学家和法律书籍著作者所注意。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永远是一种普遍的陈述。’……伯比尼安把法律描述为‘一种普遍的箴言’。乌尔比安指出,法规不是为个别人制定的,而是普遍地适用的。……而卢梭说:‘法制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约翰·奥斯丁认为,只有‘普遍地强制一个阶级去作为或不作为’的命令才是法律。”法律不论公民性别、出身、信仰、地域等方面的差别,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控制模式。
以上是从学理层面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可行性。从实践方面来看,它早已被一些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世界上现在有两个被世人公认的“花园国家”:一是欧洲的瑞士,另一个是亚洲的新加坡。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注重法治在培育社会文明中的作用。例如,在倒垃圾这件小事上,新加坡规定:乱扔垃圾,罚款1000新元,并穿上犯了罪才穿的衣服扫地一天;随地吐痰,可罚款700新元。中国许多城市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垃圾袋装化、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纸屑、不准在街头巷尾乱贴广告等一系列章程,严格管理,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