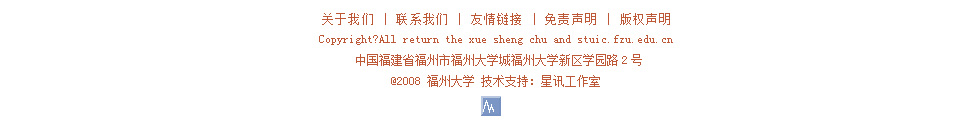最近有一起案件:一辆网约车后座被人弄脏、划破,损失大约2000元。此前曾有乘客带着一岁的孩子搭乘此车,车上留下的似是小孩的足印。司机通过滴滴公司找到该乘客,该乘客否认,司机只好报警,但有人分析说,因为没有确凿证据,恐怕维权很难。司机感叹:我国共享经济很可能被素质低的国民毁掉。对于此案,我感触颇深:我们学法律似乎学傻了,已经不会做事实认定。此案乘客什么时候上下车,司机什么时候发现座位被弄脏、划破都可以确认。网约车搭载乘客,带着孩子的乘客组合恐怕一天不会有很多次。如果不是该乘客的孩子将座椅弄脏,那么,包括该乘客的搭载者在上车时就会向司机反映,不会不言语,这是常情。另外,司机自己弄脏座椅来讹诈乘客,概率实在太低。这个事实难道真的难以认定吗?这是否反映了事实认定上的司法僵化现状?
专业主义有时带来“专业愚蠢”,专业肤浅也会带来司法僵化。我们学了法律知识,但可能学得非常浅表,懂得一点皮毛,在实践中用的结果就成了邯郸学步。如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条文众多,洋洋洒洒,里面有的规定并不合理,如法庭审判对证人询问时禁止诱导性询问的规定就缺乏科学性。即使证据规则较为严格的英美国家,也不绝对禁止诱导性询问,其一般规则是:主询问原则上禁止诱导性询问,因为证人和询问者是一方的,心理距离很近,容易被牵引作证。但也有例外,本方提问如果不是本案中实质性问题,属于边缘性问题,是可以诱导性询问的:提出了诱导性问题,对方没有反对,法官消极中立,不予干预,也等于可以进行诱导性询问:证人作证时不知道重点在哪,为了使其注意力转移到案件中有法律意义的事项上来,也可以进行诱导性询问。反询问更不用说了,诱导性询问是反询问即质证的必要方法。显然,我国司法解释规定是错误的,这说明我们对证据法的理解是浅表的。又如司法解释规定撤回起诉一个月内作不起诉的决定,殊不知撤回起诉的效力和不起诉完全相同,不能叠加,法院准予撤诉之后案件就终结,没有后续程序发展、倒流回审查起诉阶段的空间。撤回起诉,如果被告人在押,法院应该予以当庭释放;如果财物被扣押查封冻结,应由法院解除之。对于一些诉讼制度背后的原理认识不足,在司法活动中就会存在这类让司法人员浑然不觉的错误的制度设计。
狭义的“司法”,本质就是判断。法官应当是精于判断的人。司法中最难判断的就是事实。我们常常认为证据如砖,事实如墙,这样比喻其实是不确切的——事实经常很立体的,是一个建筑物,但是诉讼中事实经常被扁平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活动中,事实如果被不当剪裁,会影响决定者的正确判断。觉得不重要的事实,实际上对案件最案件最后的处理可能很重要。怎么解决这种事实不当剪裁发生的误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应当得到认真落实,这一要求涉及到直接言词原则,该原则引申出“在场原则”,要求裁判者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实质在场,裁断案件的人必须直接接触证据和当事人、证人,以便获得鲜活的心证,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
值得追问的是:司法实践中,能不能在证据短缺、事实模糊的情况下作认定呢?证据裁判原则有没有例外?答案是,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但有些事实的认定在证据之外也能作相应的认定;有些事实,可以借助推理、推定的作用来进行认定,不必依赖直接证据。有一个所罗门王的故事,说的是一名妓女睡觉时不慎将自己的婴儿压死了,她将自己的孩子和对方的婴儿换了,双方为争活着的婴儿由此发生争执。事情闹到所罗门王那里,所罗门王听了双方的陈述,也无法作出判断,于是吩咐手下说拿刀来,干脆将孩子一劈两半,分给两人。结果其中一个女人大惊,哀求说,万不可杀他;另一个却要求把孩子劈了。所罗门王就此作出评判,说活着的婴儿应当归前一个女人。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包公案中也有一个(即《包待制智勘灰阑案》)。这种通过一些事实的表现和证据,依靠推断、推理、推定、拟制等做法,建立案件事实的原貌,都是判断事实的良好的方法。
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中,尚未建立完善的推定体系。无罪推定之外,其他一些有助于推断事实的推定,司法人员熟悉的不多,比如合法性推定,内容是每个行为都视为合法做出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在这一推定下,对于合法性的质疑必须提出根据,不能仅凭想象。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存在相反的情况,控方若不能证明取证合法,就推定为不合法。此外,还存在连续性推定,即事物、情况或者位置一旦被证明在一定时期内在某种状态或者情形而存在,被推断为在合理时间里仍然依该状态或者情形连续存在。还有精神健全的推定,即每个人都被推定为神志清醒,除非有相反证据。另外,还有知法推定等许多推定。由于这些推定体系在我国法律中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我们的事实认定容易陷入僵化。
在司法活动中,除了事实认定的僵化现象外,还存在要法条主义的僵化现象,比如泉州*案件、天津大妈*案,涉及将*等和与真实的枪支同等看待,从而形成定罪和量刑上的僵化现象。公安部对枪支认定的标准设定较低,有其社会治安上的考虑。公安部设定的枪支认定标准,一旦应用于司法个案,显现过于严苛,依次裁判就失去了实质的公平性。这涉及一个问题:行政权对枪支的判断标准,司法权是否一定要受制于这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用于具体个案显现不公正时,司法司法是否有权自行厘定标准以实现司法正义。对于法条的机械应用,有时会造成实质正义的失落。例如内蒙古玉米案,农民收玉米卖给粮库从中赚一点差价,社会危害性到底在哪里?公安司法机关不考虑这些,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将被告人定罪量刑,社会舆论一起来,不得不二审改判其无罪。这类案例引出一个共性问题:社会大众都看出来这样处理案件不公正,为什么司法专业人员却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还是看出来却仍然按照司法惯性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司法僵化。
适用法律需要后天获得的理性,即法律专业教育、司法历练和社会经验积累,但学习法律之后如何让避免陷入法条主义的僵化,值得探究。阮毅成先生曾有一篇批判法学教育的旧作,认为讲求实用、速成的法律教育容易造成司法人员心灵的僵化。注重实用、速成的法条主义的法律教育,其教学方法只是在讲解条文、说明字义而已,“虽偶排有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思想史等理论功课,大都认为不足轻重”。由此“训练出来的人是谨愿之士,墨守成文,不知活用;或者偏倚之士,除条文外,不知尚有其他学问;或者保守之士,对于现行法令,不解善恶,惟知遵守;或者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能入,毫无吸取进步的可能。”他建议法律教育重视条文以外的思想原则、世界趋势和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给予学生思想的启导、民情的体解,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简单套用理解。
在当前的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有时扮演司法工匠的角色,却难以体现“工匠精神”,案件办得多了,容易陷入模式化、套路化,从而形成司法机械、僵化的现象。案件办得多、办得粗糙,就容易忽略螺丝和纽扣的差异。
人们即使认识到司法僵化的弊端,也往往难以根除司法僵化的问题,这是因为有一个根本原因不易撼动,那就是司法僵化意味着某种“安全”,惯性思维和机械司法都意味着有法条或者司法解释依据,或者司法惯性作为依托,不易出现需要司法人员担责、冒险的问题,安全感由此产生,殊不知这种“安全感”中隐伏着我们司法的危机和正义崩塌的可能。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为司法人员注入另一种“安全”,那就是司法人员的职务豁免权,培育司法人员的责任心,使其有勇气根据个案情况实现司法正义,切实体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