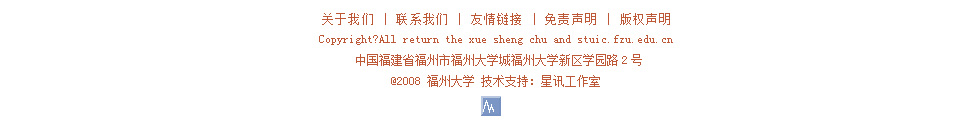几乎有了人类,便有了评论,而那些关于文学的部分,就是文学批评,到了近世,更是形成了系统严明的路径与面貌。有一种说法,文学评论、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文学,言外之意,缺失了美感、深度与创造性,那未必能称为文学批评,至少不是好的或美的文学批评。
一部作品一旦形成,包括批评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它的“读者”,面对种种评论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所有作品共同的命运。
读初中时,曾见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被逼到了忍耐的极限,脱口而出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当时不知这诗句的出处,只是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怔住了几秒钟,似乎没听懂,又似乎瞬间全都明明 白白了。后来才发现杜甫颇是写了不少这种壁立千仞的评论,其 《戏为六绝句》 除去言及“尔曹”,还写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等。它们是绝句,是诗,同时又是非常出色的关于诗歌等文学作品的评论。此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 《论诗》 也广为传布,作者是清代大史学家赵翼,他也是有建树的诗人,这样的书写者在古代不算少。像杜甫 (以及赵翼) 这样是在写诗,也是在做文学批评,结合得又近乎完美,然而今人鲜有可兼善者。也正因此,那些既是大作家大诗人又是大批评家的人是高标是典范,值得人们报以更多的敬意。
文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翻译”,同时它也可视为一种对世界和生活特殊的评论、批评,还可能是对批评的反批评,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谜之抵达,或抵达之谜。
文学面对的是自 己所身处的世界和现实生活,文学批评既要面对整个世界和现实生活这样庞然的超级文本,又要面对作家作品这一具体的文本,与此同时,作者还须得将自己放进去再升腾出来,所谓发现世界,发掘自我。所以,最后呈现出的文本,有时或者说很多时候已经偏离、远离或超出原来的作家作品,无论所面对的是主要作家还是次要作家。
文学和文学批评二者都处在世界的无限以及自身的局限之中,而且是在这无限和局限之中的一种生发。
一位小说家在与朋友聊天时赞许了我写的评论,并特别提到一个词,“有深情”。我们一起喝过酒,不过并不算很熟,而他所言确乎点到了某种东西。我深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有赖于经过淬炼的激情,以及对世界的敞开。我对自 己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有着这样的激情,而又不全是热爱,还包含怀疑与不满,甚至是挑剔与警示。具体到每一篇文学批评的写作,简而言之,我不做廉价的赞美,也不做恶意的批评,同时,也不会吝于赞美或怯于批评。“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谈论一个作家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一种虚妄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同时我以为,也不能批评一个人并不具有的缺点,而这尤为考验一个批评家的客观性与领悟力。
《蒙田随笔》“论阅历”一文中提及了批评:“我们必须有一对极硬的耳朵根才能倾听别人坦率的批评;因为很少人能够听了不感到像被咬了一口,谁大了胆子向我们提出是在对我们表现特殊的友谊;因为为了对方得益而不惜说重话伤感情,这是健康的友爱。我认为对一个缺点超过优点的人进行评价很不好办。柏拉图对于审查他人心灵的人提出三点要求:知识、善意与勇气……”我喜欢“特殊的友谊”,也希望对方不要误会“健康的友爱”,至于这“三点要求”,在知识中应包括眼界,在善意里应包括公心,在勇气里应包括准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批评也是一种自我审视。《诗品》 里有一句话颇有意味:“摇荡性情”。你的文字无论是摇荡自身的性情,还是摇荡你所面对的世界或作家作品的性情,都有摇荡在其中。《文心雕龙》 里说“抑扬乎寸心”,总有些东西会回旋起伏于心,得失寸心知,有抑有扬才是这尘世的节奏。
我们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书写,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的掣肘以及桎梏,一方面在于自己内心的是否斩截而辽阔。
英语诗人庞德有一句诗深得我心,“我的爱人像水底的火焰/难寻踪影”。“水底的火焰”这个意象,可能代表了我理想中的批评文本与批评状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那是送给这个世界,送给作者,送给愿意或能够看到这个评论的所有人的一支火焰,一支深邃的火焰。当然,也送给评论者自身。
这支水底火焰的境界为什么令我迷恋? 就像爱人一样,“她”是有难度的,幽深,难寻踪影,不易抵达,对“她”的爱有赖于体恤,更有赖于自我的沉潜、发现与创造;“她”有一种纯粹,又有一种明亮;“她”有一种穿透,又有一种魅惑;“她”意味着一种负重,一种对困难的正视,一种多重压力之下的自在生长,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巨大的轻盈……好的文学批评,始于困惑,面向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