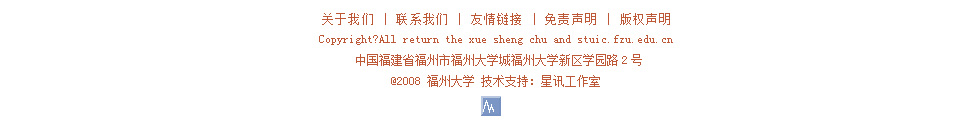我国古代法中一直有判例传统,张鷟所著判例集《龙筋凤髓判》就是典型代表。张鷟是唐代著名的律学家、文学家,其才华横溢,著述颇多。史书评价张鷟“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声名在当时就已远播海外,足见其影响之大。“新罗、日本东夷诸藩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旧唐书·张荐传附张鷟传》)《龙筋凤髓判》是张鷟最重要的法学著作,也是唐代拟判的代表。拟判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材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案件中的人物也往往匿去真名。但据霍存福考证,《龙筋凤髓判》中大多案例源于历史真实事件,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龙筋凤髓判〉判目破译》)因此,其对研究唐代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但后人对《龙筋凤髓判》不乏批评,主要认为张鷟的判词做不到“不背人情,合于法意”,甚至认为“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容斋随笔续编》)那么,《龙筋凤髓判》是否真做不到“不背人情,合于法意”?事实上,张鷟的判词虽文风华丽,但裁判说理基本做到了合于法意,兼顾人情。
一、法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律与礼是唐代主要的法律渊源,也是《龙筋凤髓判》中定罪量刑、裁判说理的主要依据。按照现代法学理论的定义,律、令、各、式类似于正式法律渊源,而礼类似于非正式法律渊源。在唐代,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而礼主要是充当裁判依据或辅助说理论证。因此,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了现代法的功能。正如严复指出西方现代“法”与中国传统“法”不能对等,“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
其一,依律定罪量刑。《唐律·断狱律》明文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龙筋凤髓判》中绝大部分案件都严格依《唐律》援引律文裁判。如“少府监二条”第一条“监贺敬盗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断两千五百里。”贺敬对判决不服,认为盗窃的垫子虽然已分在御物之内,但未上交宫廷,不能算御物。《唐律·贼盗律》规定“诸盗御宝者,绞;乘舆服御物者,流两千五百里。”注曰“谓供奉乘舆之物。服通衾、茵之属,真、副等”,即盗窃供奉皇帝的物品,服包括被、垫之类的物品,正在使用的与备用品一样都是触犯律法。张鷟在判词中也认为进贡的各类物品,只要存留在各部门,而无须上交宫廷,即可推定为御物。最后张鷟主张“法有正条,理须明典”,支持原案依律判决。
其二,依礼裁判说理。《龙筋凤髓判》中依礼裁判说理又可依有无律文规定分两种情形。1.无律文规定的情形,礼起到充当裁判依据的功能。最典型的情形是违反礼制,如“公主二条”第一条。永安公主出嫁,有司所出礼金比长公主出嫁时还多二十万,建造官邸的费用亦是如此,明显违反了贵贱长幼的次序。张鷟先从礼义的角度评论道,“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后又针对该案评论道“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少公主之礼容,岂容逾越”,委婉地表示公主出嫁不可逾越礼制。2.有律文规定的情形,礼起到说理论证的作用。唐代礼与法已高度融合,《唐律疏议·名例律·序疏》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案件说理论证离不开礼。如“左右羽林卫二条”第一条。羽林将军敬伟在皇宫有警急时不惧危险,“斫门斩关,诛锄逆贼,肃清宫禁”,得到嘉赏。张鷟却认为敬伟“论功虽则可嘉,议罪便当不敬”,“劳不足称,罪宜先结”。《唐律·卫禁律》规定“诸阑入宫门,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入上阁内者,绞;若持仗及至御在所者,斩”。敬伟在没有诏令的情况下,擅自带兵马闯入宫闱,触犯了律法。张鷟认为敬伟虽勇气可嘉,但擅自闯入宫廷,是不识君臣大体的基本礼义,功不抵过,理应处罚。
二、人情是影响裁判的因素
人情即“平凡人之心”,《龙筋凤髓判》中也体现了人情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滋贺秀三认为中国古代法中的“情”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二是“心”的意思,即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三是指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人情最接近“平凡人之心”的含义,即“一般,人们通常可以估计对方会怎样思考和行动,彼此这样相互期待,也这样相互体谅。”(《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虽然《龙筋凤髓判》大多是有关职务犯罪的“公法”,但依此定义梳理《龙筋凤髓判》也不难寻见人情的影子,主要表现三种情形:
其一,在法有明文规定时,依人情说理。此种情形下,张鷟依律判案、依情说理,情法兼顾,使判决更具说服力。如“将作监二条”第二条,少匠柳佺掌管建造三阳宫,三个月即建造完成,工匠因疲劳致死者有十五六人,但掌作官吏却因功加阶放选。《唐律擅兴律》规定“诸役功力,有所采取而不任用者,计所欠庸,坐赃论减一等”,又一步规定“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毁坏,备虑不谨,而误杀人者,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由为罪。”疏议曰“谓有所缮造营作及有所毁坏崩撤之类,不先备虑谨慎,而误杀人者,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有为罪’,或由工匠指撝,或是主司处分,各以所有为罪,明无连坐之法。”此案中,柳佺作为主管建造三阳宫的官吏,在建造宫殿的过程中,因考虑不够周到谨慎,而误致使工匠疲劳致死,明显违反律条。在判词中,张鷟认为“夫半毙而功成,若为征赏”,用工匠性命换来宫殿的建成,功不抵过,不值得称赞。他指出“法有正条,理宜科结”,应对柳佺依律处罚。张鷟先依情说理,再依律定罪,做到了情法兼顾。
其二,在法有明文规定时,依人情变通裁判。此种情形指涉案人员违反律文,但情有可原,不依律文而依人情变通裁判。如“太史刻漏二条”第一条,太史令杜淹私下教习儿子天文,并私自拥有“玄象器物”,违反律条,被人告发。《唐律·职制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注曰“私习天文者亦同”。此案明显违反律条规定,但张鷟却认为杜淹不应有罪,辩称“父为太史,子学天文”,“堂构无堕,家风不坠”,认为子承父业,其情可恕,应“准法无辜,按宜从记”。张鷟并没有拘泥于律文,而是依人情对其重新解释,做出无罪的判决。
又如“太卜太医二条”第二条,太医令张仲善开药方,私自加了三味药,和古方有出入,被判绞刑。针对配制御药中的过失犯罪《唐律》有明确规定。《唐律·名例律》规定“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属于“大不敬”,又注曰“配制御药,因过误不依本方及封签书写有错”,疏议曰“合和御药,虽凭正方,中间误谬,误违本法”。《唐律·职制律》也规定,因过失导致合和御药“不如本方”御医应处以绞刑。疏议解释“不如本方”是指分两多少不符合本方规定的情形。若是故意,则属于谋反。但张鷟在判词中认为对张仲善量刑过重,应当重新考虑律条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再予以裁判。他极力赞扬张仲善的医术,表示事出有因。同时,他也承认依律应对张仲善判处绞刑,但依人情可以原谅。“进劾断绞,亦合甘从;处方即依,诚为苦屈”,权衡之后他认为若是皇帝可以理解则情理相通,若皇帝不能理解则只能依律裁判,应衡量利弊再做出判决,表现出张鷟在法与人情之间的纠结。
其三,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人情裁判。如“苑总监二条”第一条,新安谷水社原是皇苑官地,近来被百姓吞并,苑总监奏请将百姓侵占之地再次收回苑内,百姓不服。张鷟认为新安谷水社虽是属于皇产,但应当权衡“利人”与“利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因此伤害百姓的感情,“何惜数顷之地,顿伤百姓之情”。最后张鷟认为应坚持原来宫苑与百姓田地的边界不改,依人情而裁判。
不难看出,张鷟在判词中既有对律文的娴熟运用,也有对人情的谨慎考虑,当得起“不违法意,不背人情”。因此,“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的评价有失公正。可能是因为张鷟判词中色彩风扬的文字遮盖了他审慎缜密的思维,造成了后人的误读。此外,《龙筋凤髓判》兼顾情法的特点对今日判例编撰也有启示意义,一是应鼓励非官方主体编撰判例集,有助于丰富判例研究的成果;二是编撰判例集时,选取案例不但要注重其法律价值,也要考虑其社会效果,做到法与人情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