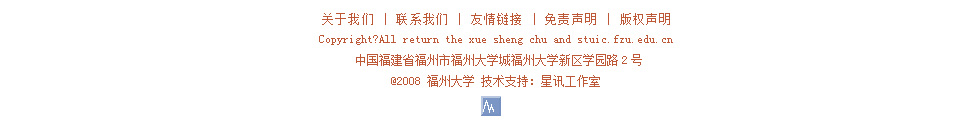作为抗战烽火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经费奇缺、安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三校的办学理念和方针各具特色。北大重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华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南开针对“大学学术恒以西洋社会为背景”的弊端,大力推行“土货化”教育,旨在将南开办成“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正是在继承、弘扬三校原有办学传统的基础上,再结合西南联大的自身实际,形成了“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西南联大精神体系。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西南联大既有“千秋耻,终当雪”的执着信念,又有“中兴业,须人杰”的强烈使命感;既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又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联大教授虽然学术背景殊异,但观点高度一致:只要保存文化,就不会灭种。为了延续文化和民族的火种,他们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再造的重任,通过教育而强化民族精神的培育,以维系民族精神的血脉。
这种文化上的自信还与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息息相关。西南联大有关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曾出现过较大争论。最终,前者占据上风,并逐步成为广大师生的共识。大家普遍认为:文理相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渗透,才能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将“在明明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中国传统的“君子”人格培养,进而承担起社会责任。
联大许多教授学贯中西,却没有食洋不化。他们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吴宓讲西洋文学、陈岱孙讲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和贺麟讲西方哲学,都能够用中国的治学方法、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书中“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而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史、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既能将中国古典语言信手拈来,又能够巧妙地将西方哲学、历史研究方法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融会其中。
不但中西贯通,而且文理交融。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了一部《中国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物理学系教授吴有训精通中国哲学;地球物理学系教授赵九章的文征明小楷极其秀雅;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刘仙洲对三国史(尤其是诸葛亮)的研究小有成就;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熟知中国历史、军事,并对时局有独到见解;另一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化学系教授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是一部道家经典著作,深受道家研究专家的推崇;数学系教授郑桐荪精于文史地理诗词;年轻的数学教授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极大地影响了莘莘学子。罗庸的“杜诗”,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通史,不但有大量文科学生选修,也受到理工科学生青睐。教室内经常座无虚席,外面还有不少人站立恭听。
文化自信进一步强化了学者们的学术自信,其突出表现是“文人相重”。许多人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却自愿向其他教授学习取经。吴宓名重联大,还时常到陈寅恪、刘文典等人的课堂上“蹭课”,且毕恭毕敬,偶尔还得站起来回答提问。哲学教授沈有鼎时常去听闻一多的《周易》、唐兰的《说文解字》和冯至的《歌德》。王竹溪也是唐兰的忠实听众。有一个学期,沈、王二人每课必到,且常常以抢到前排座位而“自鸣得意”。冯至好“蹭”陈康、冯文潜和朱自清等人的课。闻一多则是沈有鼎课堂上的常客。沈、闻二人经常激辩和切磋,一时成为联大美谈。
罗常培与朱自清学术观点迥异,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私交不薄;雷海宗、吴晗和钱穆三人同时开讲“中国通史”,他们学术上各持己见,却并不相互诋毁。中文系的《庄子》,有刘文典、闻一多、唐兰三人开讲,授课方法和观点各逞其异,彼此却相互敬重;《楚辞》一课,有闻一多、游国恩、罗庸三人开讲,大家各有轩轾,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浓情厚谊。
此外,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在内的教师发表文章、出版专著之前,一般先请有关专家审阅,“乞望”他人“挑错”和“纠谬”。历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在撰写《发羌释》时,曾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公,自感深深受益。最后,连论文题目都由罗常培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总之,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以及为复兴民族大业而培养杰出人才的责任感,不断增强西南联大舍我其谁的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争鸣,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创新活力,形成了一幅“五色交辉”、“八音合奏”的学术图景,从而创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和奇迹。(胡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