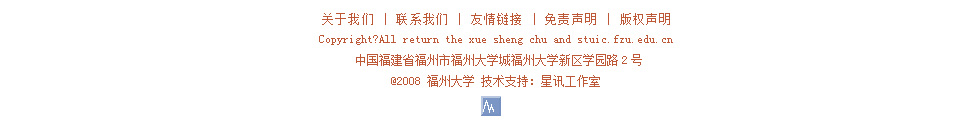深入历史现场会产生不同的批判
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认识与历史学科的建立关系很大,实际上是近代的产物,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颇有不同。今天的历史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强调新方法和工具的运用,认为由此展开研究,就能得到新知,从而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又渐渐转化为公众视野中的历史知识。
这样一条产生历史知识的线索当然很完整,但也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历史越来越成为一个“客观”的对象,仿佛与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历史并不完全是客观性的,而跟我们的主观认同也密切相关。同样一个历史事象,如果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使用不同的文字去表达,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具体到中国历史,这个矛盾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因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历史扮演着更加紧要的角色。
孔子在《论语》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把周代当作一种文明的类型,来对现实进行反观和批判。在这里,历史就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赞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把历史人物当作了一种道德的典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在历史变迁之中看到了美感。
由此可见,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历史并不仅是客观认知的对象,而且是超越感、道德感以及美感的重要来源。历史充满了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历史事实的所谓确定性,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位置。即便如《史记》这样的经典作品,其中的历史叙述也不乏饱满的文学激情。
“为己之学”延续文脉意在恢复人们的良善本性
具体再来看宋明时期,理学正是接近这段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学一词,西方汉学界的翻译是新儒学。所谓“新”,是针对孔子已降以及两汉的旧儒学而言的。新旧之间,则是长达数百年的儒学衰落期,此时风靡的是自印度入华的佛教。正如宋儒朱熹所言,“有国家者虽隆重儒学”,但“道之要妙无越于释老之中”。在朱熹看来,虽然不能够说当时的国家不重视儒学,但在那些高妙的义理方面,儒学是没有办法与佛教竞争的。
大约从中唐的韩愈开始,不断有学者致力于重新阐明儒学的义理,使之能够包容并超越佛教。宋代理学的形成,正是这一文化脉络的自然延伸。从宋初的周敦颐起,两宋理学人物涌现,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宋史》中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意思大致是:自从入科举中进士之后,朱熹任地方官只有九年、任京官只有四十天,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著述,因此是一位比较纯粹的学者。
理解朱熹的思想,比较困难的不是理学体系本身,而是他把“理”(一种包含了至善特性的抽象原则)置于宇宙本源地位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近代物理学早已指明,宇宙的运行遵循机械论的物理规则,不可能跟人的情感、社会的原则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朱熹认为,这种“天”和“人”之间的互通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才会说: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人的纯良心性,正是来源于至善的宇宙秩序。不过,朱熹同时也承认,不同人的禀赋是各有差异的,“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有些人资质极佳,“无一毫昏浊”,因此“不学而能”,即不用学习就能达到“清明纯粹”的境界。但更多的人则是“资禀既偏,又有所蔽”,因此需要“痛加工夫”,百倍用功且“进而不已”,才能最终有所成就。
朱熹还对这个下功夫的过程作了形象的比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在解释这首诗,通常是把“源头活水”理解为喻指学习,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渠”字,人们往往有错解的地方。这里的“渠”并不是“水渠”,而是作为代词指称“方塘”。朱熹的本意是用“方塘”来比喻人的内心。方塘看上去清澈透明,是因为有“源头活水”,就像人的内心,若要保持清明,则必须不断对其下功夫。
理学的本意是发展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抽象体系,从宇宙论到心性论,以便在各个方面展开与佛教的文化竞争。但最终的结果是,它落实在了儒者的“格物致知”实践之中,成为一套极为注重学习和教育的思想。朱熹最负盛名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其首篇《大学章句》的序言中就指出,设立学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性”,恢复人们被遮蔽了的良善本性。由此,这样的学习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手段。
搭乘“科举之舟”成为家读户诵的准则
或许正因为理学如此重视教育,因此在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理学先与科举制度有了深入的结合。在南宋理宗年间,“四书”被立于学宫,获得了官方教科书的地位。元代仁宗年间,科举恢复,朱熹的集注成了标准科举用书,且直至清末,沿袭不改。而搭乘“科举之舟”的理学,由此成为家读户诵的文化准则。
如同理学一样,虽然科举的作用一直饱受争议,但就促进社会流动性而言,其功效已为社会史研究所证实。明代是科举全面推行的时代,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对明代进士做过比较周详的研究。他从明代90次科举中选取了17次进行统计,涉及25000多名进士中的4700多人。按照家庭有无功名的标准,将这些进士分为四类,结果发现:这些进士大约50%来自于“白丁”家庭,即三代之内没有人获得过任何功名;而三品及以上高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进士中的比例平均不过5%。显然,这个科举系统一定程度上有着“锄强扶弱”的功能,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是有利的。
正是这些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入仕之后,常常会发展出强烈的正义感。海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相关的事例也不罕见。《明史》中记载,正德元年,宦官刘瑾弄权,蒋钦身为南京御史而“切谏”,结果“逮下诏狱,廷杖为民”。但在随后的一旬之内,蒋钦又两次“具疏”,最终竟被杖而亡。在最后一次撰写奏疏时,虽然“灯下微闻鬼声”,仿佛有先人暗中劝阻,但蒋钦依然表示“此稿不可易”,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其中不难看到理学的影响。
理学社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明显促成了基层宗族社会的发展。《家礼》是朱熹的著作之一,所论主要是士大夫的居家礼仪,涉及冠婚丧祭等日常活动。其中,尤为强调宗祠的重要性,“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此外,记录宗族活动的“谱牒”,也被认为不可或缺。
这些产生于南宋的理念和规划,到了元明时代都逐步有了落实。现存最早的谱牒于元代形成,《汪氏渊源录》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种。到了明代中后期,则出现了宗祠遍东南的局面。宗族固然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但对理学家来讲,其意义并不完全是对地方社会的整顿和治理,还隐含着用自治的方式限制皇权的意图。
理学社会化并不仅是纵向的涓滴渗透,还表现为横向的融合。元代之前,云南地区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乃至地方政权。我们去参观大理剑川县的石宝山石窟群,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一点。石窟造像基本上是佛教的概念,北方多有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但南方其实并不多见。大理的石宝山石窟兴建于9至12世纪,绵延三百年,恰好印证了当地深受佛教影响的地方文化传统。
不过,进入明代之后,石窟内的造像逐渐为碑刻和题诗取代。其中,知名的《万古胜境》诗碑即出自当地士大夫李元阳之手。他是嘉靖五年的翰林庶吉士,也是云南最早的地方志编纂人,更是理学著作《心性图说》的作者。正是这些士大夫用另一种标准重新塑造了石宝山石窟。
最后,还是回到历史意识本身。我们今天谈论历史,固然应当关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象,探究事象背后各种支配性的利益原则,但也应该关注历史情境中人们对于自身状况的理解,以及对于意义的追寻。这样,即便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会削弱“以史为鉴”的功效,但历史本身所包含的美感,还是始终会吸引人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