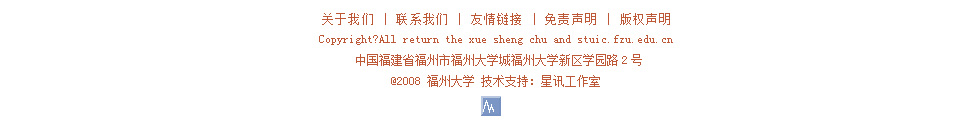鲁平同志是指引我后半段人生的导师之一。他忠心报国,生命最后一刻仍关注着“一国两制”及港澳繁荣稳定。
1987年春,我来北京兼任中国新闻社港台部主任,寄宿在北新桥三条侨办大院内的总社客房。恰好对门就是新成立的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的临时宿舍,使我有机会造访。除与鲁恭兄叙谈外,鲁平偶然也介入朋友圈。他的谈吐和风度,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都令我这来自外省的小编辑耳目一新,钦佩之至。关于“一国两制”的ABC、香港基本法起草框架、澳门过渡时期三大问题等启蒙课,我都是在那不大却充满温馨的客厅里学习的。
9月,我作为中新社代表,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中央台办和总社社长直接领导下,成功接待了首次闯入大陆公开采访的二位台湾《自立晚报》记者,一时间几个部门争相调我从事新的工作。这时,鲁平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我,并请书记李後亲自考察我。
基本法里倾注心血
1988年1月,我正式成为港澳办一员。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李後、鲁平二位秘书长领导下,在徐泽、张荣顺二位年轻但富有经验的同事支持帮助下,负责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有关事务。
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和草稿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数年前鲁平带队赴港调研后形成的中央关于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12条具体政策措施,经中英谈判载入中英联合声明附件1,成为中方对收回后的香港的承诺。基本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政策措施规定下来,全国都要遵守。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来自内地和香港的起草委员们几乎对大多数条款的草稿都意见纷呈,甚至争执得面红耳赤。鲁平牢牢把握落实“一国两制”的12条原则,随时向起草委员中的法学专家“四大护法”虚心请教,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想方设法把两地起草委员的意见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起草委员会的大大小小会议相当透明,每次都吸引了大批抢新闻的传媒界朋友。往往会议刚结束,鲁平就把文件袋交我一存,披挂上阵去会见久候在走廊里的中外记者。会议室距离记者等候区仅几十米,每跨前一步就要形成一段腹稿,犹如做“七步诗”,可是他沉着冷静,应对自如。记者们大多喜欢他,因为他有问必答,和颜悦色,凡是能公开的会议内容都会开诚布公,既客观介绍起草委员尚存的分歧,又坚定而委婉地阐明中央立场,不怕挨骂,不怕个别媒体歪曲,不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出口转内销”从而“穿上小鞋”。
在“一国两制”的两者关系中,“一国”是根本,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国”,“两制”便无从谈起。无论会场内外,鲁平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到这个观点。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草稿是争议比较多的一章,所以紧接着在第一章总则之后就拟写这章,显现了它的特别重要性。有些起草委员以为除国防、外交外,中央对香港的所有事务无管辖权,所以对草稿里把“国家行为”涵盖为“国防、外交等”的这个“等”字大惑不解。鲁平向他们解释,这个“等”就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既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拥有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也都是中央实质性任免的,那么权力属于中央的这些个“等”,不也都应该是“国家行为”、是中央应有的权力吗?
起草委员们在大前提上取得了一致,但讨论到具体条款的某提法、某措辞甚至标点符号时仍十分热烈,甚至历时几年才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注入了鲁平“坚定+灵活”的高超智慧,得来殊不容易,例如第17条关于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最终写成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该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条款,可将其发回。一旦发回立即失效,但无溯及力。“报备和发回立即失效”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立法的审批权,“无溯及力”体现了中央对特区权力的照顾。又如第23条的拟写,是在最后一次起草委员全会上才最终确定下来,既保留了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又增加了禁止“分裂国家”等内容。
经过4年8个月充分民主下的千锤百炼,两次在香港和内地广泛征求意见,对原草稿进行了100多处认真修改(其中半数以上是来自香港各界的意见建议),整部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香港基本法草案,终于在1990年2月16日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经无记名投票表决,逐条逐件获得2/3以上多数赞成通过。为了庆祝获得中国立法史没有前例的圆满成果,当晚,全体起草委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举行大联欢,李後、鲁平二位秘书长高高兴兴地和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登台,合唱脍炙人口的《歌唱祖国》和贝多芬的《欢乐颂》。曲目是由鲁平审定的,还指定我担任这次合唱的指挥。台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二位秘书长在草案稿里倾注了多少心血。几周前,鲁平还一再督促检查应出席的55位起草委员能否如期出席的详细情况,有位起草委员正在加拿大作学术研究,不便提前回国,鲁平亲自给他打电话说明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为他联系业务主管部门和其他多个部门,排除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困难,满足了包括经济补偿、物资待遇方面(例如出入境不满1年仍有权一次性购买“三大件”)的现实需求,终于多争取到一位起草委员的投票权。
第二天上午,雪后放晴,空气清新,北京人民大会堂屋顶上银辉耀眼。中央领导人在这里接见全体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上午10时,邓小平同志步入东大厅,在热烈的掌声中即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你们经过将近5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杰作。”小平同志刚开讲,鲁平示意我赶紧记录。接见结束,我立即整理记录稿,经审定后中午就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闭幕式。我跟随鲁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二楼,观摩全体人大代表审议表决通过香港基本法草案。当主席团宣布香港基本法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时,鲁平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使劲鼓掌,两行晶莹的泪水从眼镜片下方滑至两腮。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落泪。
难怪孝子鲁恭在八宝山父亲骨灰龛里安放的两件陪伴物之一,就是一本中英文的香港基本法。
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1989年后,处心积虑“光荣撤退”的英方在未与中方作任何商量的情况下,倾港英政府全部财力外加未来特区政府须背负庞大债务,抛出一个“新机场建设计划”。香港确实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新机场,早在80年代初中方就已向英方提出过,但被置之不理多年。现在,这新机场能这样建吗?为什么工程设计费用几乎已被英资顾问公司“包圆”了?
针对港英政府1997/98年度的财政预算,只准备留下远不敷特区开张的50亿港元,国务院港澳办鲁平主任着急了,他面对众多媒体连声责问英方“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3个“怎么办”,从此成为了香港过渡时期流传官场、民间的口头禅。
随着推进机场建设的单方面努力处处碰壁,英方尝到了没有中方合作真办不成大事的苦头,终于回到谈判桌旁。我作为中国政府工作小组组长,与英国外交部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等谈了几轮还是谈不拢。
时间到了1991年6月27日,高手出场的时候。英国特使、首相外事顾问科利达携带新的方案,绕道他国秘密飞来北京。他的谈判对手正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
这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曾经出任驻华大使,回国后担任两任首相外事顾问。我至今记得,谈判一开始,他的眼睛像老鹰一样尖锐地直视鲁平,两分钟内一语不发。鲁平更沉着应战,迎向科利达的目光,也紧闭双唇不开腔,直到对方收回目光为止。由于英方带来的新方案基本满足了中方对未来香港特区财政状况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英方接受了中方依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2延伸出来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在香港过渡时期,凡是跨越1997年的事务必须由中英双方磋商一致方可办理。经过两天舌尖上的外交,双方终于就香港新机场建设的安排及有关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共识。
科利达建议立刻签正式协议。鲁平说:“且慢,这么重要的协议我俩只能草签,正式协议得由两国政府首脑来签署。”
科利达一听觉得中方有意加码,火了:“那就拉倒,不签了!”说完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
鲁平并不为所动,对这种语带情绪的威胁甚至不屑在意,他看我有些沉不住气,肯定地说:“科利达会回来的。”
曾经一段时期,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偶有高层外交往来也尽量不与中国政府领导人握手。这次香港新机场协议如能把英国首相调度到北京,与中国总理一同签署,意义当然非同一般。而对于英方来说,这是在香港过渡时期与中国修复关系的重要契机,否则香港的管治还将步履维艰,所以不会轻言放弃。仅隔数小时,科利达就来要求复会,并答允梅杰首相不久将访华,和李鹏总理签协议。
翌日是6月30日———离英国交还香港还有整整6个年头。凌晨5时,我轻轻敲开鲁平的房门,把连夜整理并清稿打印了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中文稿呈请他审阅。他笑吟吟地递给我一首刚填写的词《卜算子》,我先睹为快:“雨扣榻前窗,风扰伊人觉,已是更深夜静时,何事争相报。晨起万空晴,鹊雀声声早,只见青遍柳树梢,方晓春之到。”
上午,以“特急件”呈报中央领导的请示很快获得批复同意。鲁平主任和科利达特使随即在长长的谈判桌两头,在一式两份的中英文本每一页边沿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弥漫着香槟酒的香气。科利达举着高脚酒杯,难得一笑,对鲁平说:“你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鲁平也还以微笑说:“你也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不忘初心正气凛然的榜样
无论在殚精竭虑力争完整收回香港的日子里,还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春夏秋冬,无论在职还是离休,鲁平不忘初心,始终国而忘私、正气凛然,是我的好榜样。在中英新机场谈判后的一系列关于香港过渡、政权交接的谈判中,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背信弃义推行“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后,鲁平和周南等同志遵照小平同志“另起炉灶”的重要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建议中央出台提前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以及提前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等反制举措,为重建战略主动态势、最终完整地收回香港提供了可靠保障。
2012年春,我完成了纪实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初稿,第一时间发往鲁平的邮箱,请他阅正。大约一周后,收到了让我备受鼓舞的回复:“读完了你的大作,感慨万千。你以生动的笔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画了那个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惊心动魄的年代。它是一部优秀的、可读性和史料性都很强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内地和香港的欢迎,争相一睹为快。”
这年7月1日下午,香港反对派的游行队伍里首次出现港英时代的英国米字旗,喊出了要分离祖国的港独口号。不久,港独分子又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门前,挥舞米字旗,唱英国国歌,呼喊“南京条约万岁”,打出了“中国不会给我们真正的自治,唯一出路是独立建国”的反动标语。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大篇幅地图文报道。85岁的鲁平再次被激怒了。他给《华盛顿邮报》发去一则电邮,要求全文刊登:“这些鼓吹香港独立的人是纯粹的白痴,没有内地的支持,香港就会变成一座死城。他们知道每天喝的水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或许自以为比英国人聪明。为什么英国人最后选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而不是宣称让它独立呢?”这家美国报纸未刊登鲁平评论。鲁平又把邮件发给我,我立刻响应共鸣,在我的香港新书发布会上,回答读者提问时引用鲁主任的评论,说:“我感到痛心,那面米字旗本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而不应该再出现在街头。”我还把鲁平的评论译成中文,托香港媒体朋友予以发表,最后仅有《南华早报》发表了,用的仍是英文。
热爱事业热爱团队热爱生活
鲁平热爱“一国两制”事业,时时关注着香港、澳门,像守卫国门的哨兵一样。他每天要读十几份左中右的港澳中英文报纸,往往能从别人不经意的字里行间敏锐发现对手的新动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导我:“像下象棋——和老谋深算的殖民主义者打交道,你走一步要看三步。”也许因此,对手们都对他敬而生畏,连被他斥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东方与西方》中欣赏他的聪明、出众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中国的政治让我们之间只能拥抱像默剧一样的敌意。”
正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让鲁平和他的团队在中央正确领导下胜利迎来了港澳回归。他爱护并且信任自己的团队。一旦办公会议议定了事,就放手让司处长们各司其职,往年轻同事肩上多压担子。在办公楼里他是不苟言笑的,对犯了错的人———包括对我的批评教育,是不留情面的,治病救人的。我这一辈同事以及更年轻的与他忘年交的同事们,都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教授而不是部长,我们欣赏他满头漂亮的银发、语出惊人又合情理的答记者问,我们喜欢跟随他矍铄脸庞上的喜怒哀乐,有时心悦诚服,有时颤颤紧紧。“鲁平同志”———多年以来港澳办上下几乎都这样称呼他,称呼里蓄含尊敬和爱戴。鲁平对于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年届古稀又大病初愈,却担当着统领香港回归“参谋部”这样宏大繁重的责任。上率下行,每天早晨八点前他必定踏进办公室,该做的事情一定当天做完,做不完就加班加点,直到办公桌面上干干净净,没有一张积压的文件纸,才提起公文包离开。所以,1997年上半年的几乎每个夜晚,国务院港澳办机关大楼的每扇窗户都灯火通明。
下了班,回到侨办、港澳办干部合住的甘家口塔楼公寓,他又变得十分和气,见人笑吟吟地打招呼。他年轻时就喜欢捣鼓电器、机械,大学学的专业也是农机,“文革”中赋闲在干校,常骑着自行车帮人修理收音机。所以,公寓里楼道的电闸保险丝断了,谁家的电灯不亮了,他都会热心及时施援。遇上节假日,偶然放松下来,还会招呼左邻右舍的同事一起来聚个餐,各家出一盘菜,南北风味大荟萃。
他热爱生活,是一位水准很高的音乐爱好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CD还不普及,他家里摆满了古典交响乐的录音磁带,同一曲目的作品可能有好几盒磁带,是由世界不同乐团不同指挥家演奏的。他曾说,那些收集来的磁带是家里最大的财富。每次谈交响乐他都津津乐道,对我弟弟、中国第一个交响乐指挥博士陈佐湟的兴趣比对我大得多。他常叹息说:“香港还没回归,能腾出来欣赏交响乐的时间太少了。”
而香港回归后,他又迷上了电脑,每天在小小的屏幕前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收发e-mail,关注天下大事、港澳动态。
2015年元旦刚过,他从珠海回北京,到北京医院北楼查体,说腰背持续疼痛,可能扭伤了。不料经医生和CT仪器仔细诊断,竟是胰腺癌晚期了。原来只为查体准备住一两天院的,却不得不继续住下去。我多次看望他,他都不愿多谈病况,不愿多麻烦医院和港澳办机关。反而常常问些全国港澳研究会的近期活动,专家学者们对局势又有什么独到看法。有一天,我坐在他的病榻旁,他沉默了一会儿,郑重地向我交代了三件事:一、鲁师母开始有老年痴呆的现象,担心走在了师母前面。以后帮她找个好的保姆。二、秘书小韩是个优秀青年,去香港大学进修过,帮他成长为好的港澳业务干部。三、完全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拥护习总书记和中央对港澳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白皮书写得很好。要痛下决心,对照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总结和反思过往的工作……
鲁恭兄嘱我写篇纪念文字。半生桃李之教,顿时涌上心头,仿佛又听见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哀丝豪竹声中,逝者如斯,发人深省。愿“一国两制”事业蒸蒸日上,香港澳门特区繁荣稳定,这应是对鲁师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