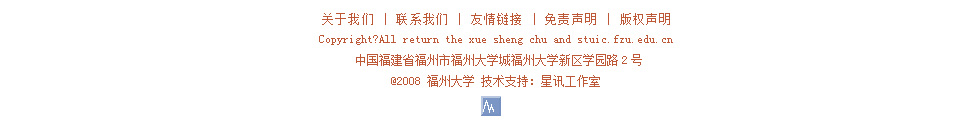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唐宋”仿佛早已成为一个关于历史时段的固定词汇,在过去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里面,大家经常把“唐宋”放在一起讨论。随意举一些例子,在中国学者中,比如像柳诒徵、钱穆、傅乐成[1],在美国方面,已经译成中文的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就是把唐宋连在一起讨论的[2]。而日本方面,则可以看宫泽知之的《唐宋社会变革论》以及丸桥充拓的《唐宋变革史研究近况》的介绍[3]。很显然,“唐宋”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意味的时段,以这个时段来研究历史的观念至今还是主流,就在2001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关于“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佛教与社会”的国际讨论会,都是以“唐宋”为一个时间段的,而在2002年,厦门大学与浙江大学都召开了有关唐宋历史的学术会议,主要议题都与唐宋社会变迁相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把“唐宋”放在一起作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也许是因为两个意味相反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唐宋历史的“连续”。在人们普遍的历史感觉中,唐宋有一种连续意味,不仅仅是因为古代人就已经看到,从政区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各个方面,宋代都延续了唐代,于是把唐宋连在一起,说“宋承唐制”,而且,从一般的历史感觉上,唐宋也是古代中国两个文化和思想上都值得推崇的鼎盛时代,说“唐诗宋词”也好,说“唐宋传奇”也好,有过李白杜甫王维的那个盛世,和《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时代,也还是能互相接续的,所以“唐宋”就这样仿佛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标志一种对于历史的连续记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习惯地把这两个朝代放在一起[4]。另一个原因却相反,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唐宋历史的“断裂”。从很早以来,就有人意识到唐和宋的不同,但大多是直觉把握或笼统感受,并没有理性地提出可供分析的框架,直到日本的内藤湖南,才根据西洋史的理论,明确地提出一种理论,把唐算作“中古”的结束,而把宋看成“近世”的开始。如果看他那篇引起很多争议的《支那论》和《唐宋时代的概观》就可以知道,他是站在后世回头看,发现唐代还是贵族社会,而宋代是君主独裁与平民主义的社会,而晚唐五代是一个过渡期。从唐到宋,前后两个时代,一切都不同了,所以,唐宋成了中古和近世的分水岭。这种意见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后来他的学生宫崎市定更把这一说法具体化,补充了很多很多方面的证据,而且很多人凭着读史的经验,更提出了以安史之乱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看法。在中国,像陈寅恪《论韩愈》就是这个看法,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也是这个看法[5]。但是,正是因为唐宋的巨大差异,反而在研究中把这两个时代连在一起了,唐代始终是宋代存在的巨大背景,而宋代则始终是唐代的历史延续,不仅是历史与思想,也包括文学[6]。因此,这种断裂反而使唐宋更连成了一个时段。
早就有人指出过这一微妙处,1918年傅斯年有一篇讨论中国历史分期的文章指出,唐宋两代的历史是既断裂又连续,“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7],这话很有意思,所以,唐宋变革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最近,有学者呼吁要有兼通宋史的人来研究唐史[8],这是很对的,其实研究宋史的人,常常也会关心唐史,研究历史的人总是要做历史寻根的,没有因,哪有果呢? 具体到文化史、思想史研究里面来说,这种看法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把唐宋连在一起,就可以发现和解释很多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比如,盛唐以后对于孟子的升格运动,使上层儒家思想的方向从荀子强调“礼法”一路,转向孟子一路的“性善”、“良知”、“好辩”,引起了刘子健说的“中国转向内在”,确立了宋代重视“内在超越”的路数[9];比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原道》开创了宋代新儒家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历史,而他的学生李翱的《复性书》结合儒释两家的说法,把儒家的道德约束从外在转向内在,结果是使佛教理论进入儒家学说,而新的儒家学说有效地超越和涵盖了佛教,同时也有效地取代和抵制了佛教。再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宋代有怀疑经典可靠性的风气,这种风气可以追溯到中唐时代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质疑《春秋》三传,它影响了宋代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甚至开创了宋代很有近代意味的学术风气[10]。而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开始的变礼迭出、仪注盛行,也改变了传统的经典之礼,使礼仪与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得到改变,以致于影响到了宋代[11]。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都是从唐代开始萌芽,到了宋代开始变成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唐宋之不同,恰恰更使唐宋历史联系在一起,套用一篇论文的名字,也可以说是“没有中唐,何来两宋”[12]。
文化史与思想史指出的这种现象,得到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各方面资料的支持,比如说,贵族社会的瓦解,科举制度造成的社会阶层流动,家族重建中形成的新的士绅阶层,都成了解释这些文化思想变化的背景。我们举包弼德(PeterBol)的书为例[13],他的分析思路就是这样的:由于八世纪以后,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帝国分裂和藩镇叛乱,使一切成了“不确定的世界,其中规范性的典范至多不过是临时的,圣人的意图也成了需要阐释的东西”,所以,士人深切感到需要挽救“斯文”,这个“斯文”用包弼德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文化”,因此才开始产生了后来的“道学”或者叫“理学”,当一部分士人越来越倾向于“理”和“心”的时候,文化当然转向了“内在”,因为,在政治层面真正起作用的、外在的现实主义策略和制度,逐渐在意识或观念中被认为,这是次要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应当是超越具体的“天理”、“心性”。而这一切变化,又和社会背景的变化有关,他分析说,因为唐代社会给一般读书人提供了宽松空间和多元途径,包括科举入仕、藩镇延揽人才,使得很多优秀的士人可以冲击门阀贵族,并使得垄断知识资源的贵族瓦解,贵族社会的色彩也越来越淡化,这种现象,也使过去垄断知识和真理、熟悉外在仪节、依赖血缘系统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贵族社会,转向了依赖学习和努力、重视内在修养和精神、强调平民主义的士绅社会。根据他的分析,从唐到宋,首先,是意义和价值的宇宙依据发生了变化,从“天”到“理”,其次,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古”即历史作为证明,到“心灵”或“观念”作为依据[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