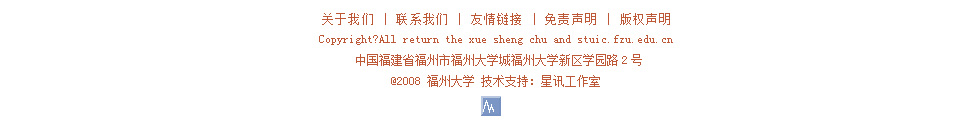我于1971年开始学汉语,1974年开始做汉学研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最感兴趣的领域是欧洲中古时代到20世纪初的叙事文学与小说。为什么学起汉语来了呢?在主修法语以前,我先主修语言学,而语言学系的学生按照规定都得学一门非欧洲语言系统的外语,我于是就选择了汉语。在这之前,我对中国一点印象都没有,吸引我的是一个较抽象的“目标”:学一门与自己的母语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这么选择会给我一定挑战和机会,让我迈入一个对惯性思维极具刺激性的世界,说不定也会让我“成为”(或“懂得”)另外一个“人种”,进入一个超越性的意识境界。我这样想,跟当时流行整个美国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潮流有关。当时很多人通过吸食*(尤其是LSD)来达到此目的,也有不少人借助禅坐、清修,及其他许多办法,如政治活动、读书学习等来进行,我选择了后者——读书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选择所造成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是1976—1977年我去台湾留学。我在台北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住宿则在国际学社。住的是一间有四个床位的房间,有三位来自台湾本土的同屋。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个新词汇就好像是一张新门票,那么多门票就好像每天有一千扇大门在不断地对我次第打开,有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
这种过瘾的感觉,竟然还有第二次,是1979—1981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时。中美建交的第二年,我作为第二批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研究生到中国来学习。汉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当时变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个美国人研究法国文学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政治影响。但一个美国人若研究中国,则会极不一样。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主要是到日本或中国台湾去,到中国大陆来,是1979年之后才有的可能。在台湾读书时,跟语言学校的老师交流,我受到了一些国民党的宣传,“光复大陆”、“勿忘在莒”之类的标语,在台湾街头及宣传品里,随处可以看到,“孔孟之道”也听了不少。同时也听到了很多迄今都令人尤为感动的人生经历。几乎我的所有台湾老师都是从大陆过来的,他们常常提到抗战前后与逃离大陆的故事,再加上我在台湾学习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忘年交”,——不是一起学习的台湾同学,是一位50多岁、来自山东的退伍老兵老宋(我已在别处写过他的传),他当时在国际学社当工友。他跟我讲了很多国共战场和山东老家的事。我当时对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都了解得很肤浅,而且也不感兴趣。——这可能不像当时其他的一些美国同学,他们有的甚至热爱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极为瞩目关注。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不能不去了解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复旦的同学与我来往多的,基本都是1977级。他们大部分刚从乡下或工厂出来,其中也有几位作家,包括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作家(如写《伤痕》和《拂晓前的葬礼》的两位,就都是当时复旦中文系的本科生,而且后者到现在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个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么一种环境,真像是进入了另一宇宙一样。当时我跟人交流有极度陌生感,生活条件又极其艰苦,每有不舒服与不适应,但也有很多快乐,尤其是认识新朋友时。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离得越远,那种新鲜感就越强烈。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在那时候还是一个禁区(今天可能稍好),尤其是像《金瓶梅》之类的作品。美国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读这些小说,中国长期以来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人纵深研究这类小说。有一位很权威的普林斯顿教授很早就曾跟我说过,研究这类题目就好比是把中国的脏衣服晾在外面给大家看。他是开玩笑,但也不完全是开玩笑。背后大家有疑问:写性这个题目是不是太不严肃?是不是太好玩?别的同学很用功地研究很正经的问题,像顾炎武的政治思想、明代的北京、清代的户口制度等等,而我关注及诉诸研究的,则是明清世情与色情小说。
简而言之,我在当时只好自己“开辟”自己的研究道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阅览旧小说,也从上海跑了无数次北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善本。那样的小说没处买,一般图书馆也不对外借阅,只能在阅览室一本一本地读;而且读完了书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一起讨论,因为“性”这个题目,大家还是比较忌讳的,在当时也很少有人会读这样的书;再加上连我自己当时对性与性别研究也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储备,还缺少方向与理论的训练,我第一次发现有《金瓶梅》这么一本书时,极度吃惊,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后来发现的“新大陆”越来越多,一跳进去就是一个“无底洞”。不但有《金瓶梅》,还有很多类似的小说,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也包括许多小说集,如《欢喜冤家》《一片情》《弁而钗》,等等,更不用说有什么《如意君传》《绣榻野史》《肉蒲团》等等比前者更为色情的小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但过去很少有人予以很多关注。于是我就开始了两种互不连属的研究生活:一是跟中国朋友和中国老师交流,讨论正经文学文本;其二是我的个人研究专题,只能自己跟自己探讨。有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1979—1981年在复旦进修,1985—1986年在北大作访问学者,两次都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资助;1987、1988、1989,连续三年,每年夏天我都到北大访书、访学,同时也访旧,与旧日师友见面、交流;1991年我最后一次在北大作了一年的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访问学者,这期间我都一直在读明清的世情与色情小说,进行思考、研究。从1991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我都会到中国一次,每次两三个星期,见见老朋友,也与中国的同行交流、互换研究心得。
30年来,我慢慢地总结并形成了一套研究性与性别的方法。我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一个尴尬的、比较别扭的题目作为研究专题。这并不简单,还极不容易。用计算的方法来数一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每人有多少次上床机会,某某人跟多少对象发生过性关系,或者数一数旧小说中有多少字是秽亵的、需要删节的……这都没有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小说中语言的用法,比如性行为的描写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是暗示的、轻描淡写的还是露骨的、毫无顾忌的?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在理论上如何讨论性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总的来说,一个忌讳的、被封闭的题目总是有很多成见妨碍我们去了解它。幸亏20世纪中后期有许多理论帮了我很大的忙: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它们最重要的贡献,也即它们的一个主要共同点,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性的质疑。女性主义给我的启发是关于男性主导价值观对女性的各种排斥与成见,以及社会对性别角色所起的支配作用。我逐渐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也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起主要的支配作用,这即是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女人身体的买卖以及青楼文化也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妓女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在旧小说当中,正妻与妾的关系,她们之间的互相争斗、交往、妥协、合作,以及她们的不同用心与动机,都引发我极大的好奇与兴趣。他们各自所属的人物类型,也时时引发我的注意,如奇女子、淫妇、泼妇、吝啬鬼、酒肉和尚、败家子、风流才子、落魄书生、侠客、贤妻良母,等等。另外还有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在晚清,当中国受到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妻妾制度逐步发生的变化,都在我的关注之中。最近我所作的新的研究,是中国历代皇帝的后妃制度。后妃制度在每一个朝代所发生的故事、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皇后(或太后)的“垂帘听政”与她们在历史上对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我的着眼点。比如对慈禧太后,我们今天的研究视角、眼光、问题意识,肯定和十几二十年以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