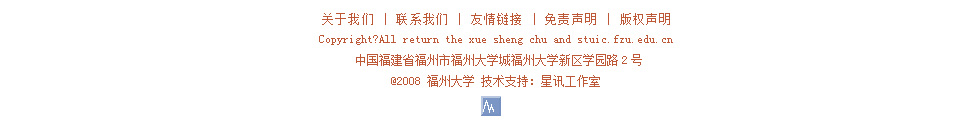包华石看到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渐渐发展到比较性研究,并指出这个趋势跟欧洲美术史的演变也分不开——研究欧洲美术史的学者跟汉学家们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的。
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在“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讲座中主要介绍了欧洲、美国艺术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情况。
包华石开宗明义地提出外国艺术史家的观点一定会受到文化政治的影响,不可能纯粹中立,并引用曹意强在《艺术与历史》中的论点:“在19世纪的学术界,艺术是开启往昔的一把钥匙,这一信仰激发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历史放在艺术繁荣的中心地位,例如,米什莱声称文艺复兴在法国而非在意大利达到了巅峰。”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宣称每一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反映其文化的基本特色,譬如古代埃及艺术风格一般很呆板,而古希腊的雕塑流畅而自然(即写实)。如何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显得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秀,以艺术史来体现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黑格尔也是如此,他认为文化的巅峰是在德国。黑格尔民族精神的说法出现后,不少德国学者企图用艺术史来证明欧洲的或者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全球最优秀的。西方艺术史学历来被用作民族主义的武器。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很多西方学者对东方、中东、非洲的态度是四海为家的观点。
包华石进一步指出,自19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艺术的学科是与现代艺术的发展并行的。古典的欧洲绘画论认为艺术的目标是模仿真实,到19世纪中期有一批欧洲画家想摆脱这种写实主义的约束,其中不少就借用了日本和中国画家的技法。比如惠斯勒后期的绘画是现代化、日本化、国际化的;还有如卡萨特前后期画风的变化;罗特列克早期和后期作品风格的改变;喜多川歌麿对莫奈的影响;歌川广重对Henri Riviere的影响;梵高对歌川广重的《大桥骤雨》直接的摹写等。然而,虽然有现
代性的艺术品出现,但此时还没有产生理论的支持。罗杰·弗莱(Roger Fry)和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就是要解决这方面的理论问题。比尼恩在1908年一本关于东方艺术的著作里写道:“In the art of T’ang, there was a conscious effort to unite calligraphy with painting. By this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painters strove for expression through brush-work which had at once the life-communicating power of the lines that suggest the living forms of reality and the rhythmical beauty inherent in the modulated sweep of a masterly writer.”文章里的rhythm来自中国古典画论里的“气韵”一词。弗莱用这个观念来建立一个核心观点,即一个抽象的线条本身虽然没有描绘出任何物体,但还是可以传达画家的感情——这对于现代艺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看法。弗莱对rhythm看法的来源是郭若虚,由此他解决了现代艺术家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抽象的形状表达内容,同时他也给现代艺术史研究领域打下了基础。弗莱用这个方法建立了所谓的“形式主义”,艺术史家开始用此分析文艺复兴的艺术品,以及中国的、非洲的艺术品。当时的西方艺术史家很看好中国,比如他们会说,能画出流畅线条的波提切利是中国式的画家,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纳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高涨,使得艺术史家不能再说这类观念来自中国了。
接下来,包华石介绍了三代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西方学者。第一代学者出现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Hugo Munsterberg、Ludwig Bachhofer、 Leroy Davidson,这三位学者都看不懂中文,此时西方的汉学研究还没有专业化。20世纪30到60年代,很多艺术史家都认为艺术演变的目的是要越来越写实,但Bachhofer认为艺术演变的目的不是写实,每个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而艺术风格会反映他们的价值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第二次亚洲艺术热,出现如Jackson Pollock、Franz Kline、David Smith、Robert Motherwell等艺术家。与此同时,涌现了第二代研究中国艺术的西方学者,如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方闻、斯德本(Harrie Vanderstappen)和艾瑞慈(Richard Edwards)。高居翰(James Cahill)1960年代初期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属于德国世系,对社会艺术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代学者精通中文、日文,并且到东方学习了中国传统鉴赏方法,如辨识题款、题跋、印章等,将欧美形式主义和中国的传统鉴定方法融合到一起。他们给美国的中国艺术史领域的研究打下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方向,即:进行基本的鉴赏研究,包括题款、题跋、印章等;发表关于伟大画家的专题论文;举办展览让美国观众多多欣赏中国的文化成就;初步从事编写中国绘画通史的工作。第三代(1960年代)学者包括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李雪曼(Sherman E.Lee)、何惠鉴、李铸晋。1962年,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赞助人与画家》一书出版,社会艺术史由此开始。直到1980年代晚期,学者也基本上都是采用社会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新一代学者有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巫鸿、柯律格(Craig Clunas)、乔迅(Jonanthan Hay)等人。柯律格1991年的著作标志着艺术史研究进入下一个学术阶段,即将欧洲和中国的艺术史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包华石提到,最近也有历史学家进行了全球性的比较研究,包括Bin Wong、 Kenneth Pomerantz、 Richard Vinograd、Haun Saussy、Joan Kee、J.P. Park、Winnie Wong,他们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研究中国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演讲的最后,包华石介绍了《中国艺术指南》(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t,包华石与Katherine R. Tsiang编,Wiley-Blackwell,2015)一书,有助于更多地了解美国、英国学者,以及在美国任教的东方学者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看法。
讨论阶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指出,如今很多年轻学子不必对西方研究盲目崇拜,要更注意搜集、理解材料,并提醒年轻学子要多读书,重要文献要反复读。他指出考古学很伟大,但不能揭示所有问题,文献反而可以解说一些考古学不能解说的东西,比如6世纪中期到8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现象是联珠纹。关于联珠纹织物的考古发现,已知最早在吐鲁番阿斯塔纳558年墓。联珠纹是从西往东传播的,那么在西边的发现应该更早,可是按《北齐书》的记录,更早的时间点543年就在太原出现。所以不能把艺术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一定要用历史文献来补充解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针对尚刚教授的发言进行补充,提到关于中国画家的小册子,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林泉丘壑》(再版将更名为《烟霞丘壑》)。李凇谈到西方的主流艺术史研究并不太关注中国工艺美术,可西方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甚至德国斯图加特的Linden Museum这样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也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工艺品。在材料的获取方面,西方博物馆比国内的博物馆给学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提醒青年学子不仅要仔细理解材料,还要掌握原始文献,不要依赖于电脑检索,那会导致断章取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从专业角度出发,谈到对德国艺术史传统的看法,认为各个民族在争相认领自己是合法性的代表时,反而将艺术史的价值相对化了。在贡布里希著作引进之后,人们对民族主义一直有负面的评价,可是从历史来看,民族主义在普泛化,民族主义的艺术史学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不断地碎片化,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声张自己的合法性,声张它自己的价值和叙述方式,然而事实是很多情况下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并进而对艺术史分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包华石针对评议进行回应和补充,他指出“欧洲中心论”并不是说欧洲人喜欢研究欧洲艺术,而是指欧洲人认为历史上所有重要发现都是白人产生的。并进一步补充,指出其分类方法在按照年代划分的同时也会根据方法。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阶段,当时弗莱、马蒂斯对于东方的看法很正面,弗莱的形式主义可以超越不同的文化,按他的方法,即便不是研究非洲的专家,也可以讨论非洲艺术。所以从那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的方法都是形式主义,因为30、40年代的学者不会中文,他们必须使用形式主义;而到了高居翰、苏利文的时代,学者们能看懂中文,并且在中国学习生活。包华石看到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渐渐发展到比较性研究,并指出这个趋势跟欧洲美术史的演变也分不开——研究欧洲美术史的学者跟汉学家们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强根据自己在美国求学、工作的经历,谈到社会艺术史时期,很多方法借鉴自汉学研究,且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方法也来自西方美术史的方法。因此,宁强认为与其学习二手的研究方法,不如直接学习西方学者研究文艺复兴、罗马艺术、法国绘画的方法。他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西方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做美术史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联系更为紧密,且有历史文献的记载支撑,应该回到本源,更多从中国传统历史学、传统考古学这里面来寻求一些方法论上的启发。
包华石针对宁强的发言做出解释,西方的研究社会艺术史的方法并不是来自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学者。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有学者研究社会艺术史,其后有何惠鉴、李铸晋等人也在进行,这比贡布里希、哈斯克尔更早,两者在方法上是平行的。包华石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用到的社会艺术史的方法是通过看文物考古的杂志向中国学者学得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青生针对包华石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补充,指出艺术史的前提是这件物品要成为史料,而作为史料有两个前提,一是它看起来要是真实的,二是表面的形态背后藏有意义,这是西方艺术的特质。中国艺术也可能有,但如果按这个思路研究,那研究的未必是中国艺术,可能是中国可以作为艺术史的部分史料。朱青生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对艺术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用一种方法研究所有问题,要重新研究。另外有个潜在问题——艺术难道只有艺术史可以研究吗?这样一问甚至可以推论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反历史,如果把艺术当作史料研究,就是对艺术本身一些性质的否定。
提问环节,听众提出问题——在美国,是否有史学史的科目存在,且有意地用这种理论推动艺术史的发展?包华石解答,这种研究在美国很流行。美国关于艺术史的杂志有不少这类论文,很多艺术史系通常会有一两位学者专门做这方面研究。艺术史基本上算是历史的一个专业,艺术史学者其实应该在历史系,本质上都是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