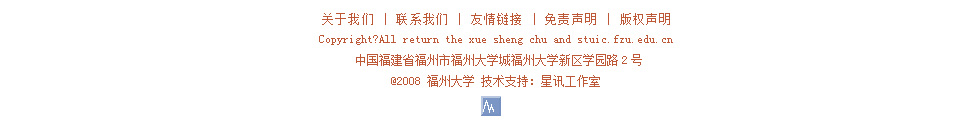去年秋天,在鲁迅文学院,我和江子享用过纯度交流。他叫我老哥,有时叫大哥和老师。江子喜欢打台球。我跟他打台球时候,仰面看清了他的心象,他让我步入民间最亲柔的腹地,把他的故乡视为火炬,照耀我的绿色梦想。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完《在谶语中练习击球》之后,更加认定江子曾经拥有的沉着和悠闲。他曾经在江西吉水的一个小镇,通过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和内在信念,体验过一种独立而具有精神高度的生存状态。诚如我曾对何述强所言,江子的文字温婉细腻,他的写作浸润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一种可欲望的精微锐利的艺术感觉,使他用适合自己的耐心、睿智和灵动的确定形式,充分展现了他独具一格的散文才华。
江子对生活经验的提示,当然来自他的思想和体验,也来自他能把握现实的复杂性和悖论式情境。从他的信念和趣味中,可以看出他不像过路的吟唱者,只关心闪电和急雨,他知道抒情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的控制。在独到的人性分析中,江子明白谁在他人的故乡,与反常的智士彻夜风流,那些隐晦的短信,仅仅发给人造美女听取的。在令人着迷的文坛,骚体写作者亮星般破空而出。忧心的江子愈见孤单,经常在内心燃起黑夜。这也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哲学,贯穿于他的写作始终的是灵魂的倾诉,既有忧伤的和绚丽的,也有热烈的和偏执的,但他那烂漫的倾诉散文,并没有伤感而失去人性的力量,他天衣无缝地把灵魂倾诉和哲学分析融合起来,不仅构成一种神秘的情感穿透力,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把人们引向理性的断裂边界,一眼就能看出善与恶的属性。
江子崛起于文坛,与审美霸权体系没有紧密而直接关系,属于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身,他不再相信某种大一统的独尊话语体系,当然也不尊奉旧有的文学典律。我也以为文学作品不是战利品,也不是深度知识、女性子宫和金果子,而是应被看作通向心灵的一条伟大道路,简而言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江子的文本是语码,表明他在意识形态上是纯洁的,只描写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不描写下半身的意义。所以我有理由说,江子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散文家,他的勇敢和孤独,曾获得了广泛赞誉,但《在谶语中练习击球》是一部很低调的散文集,这跟他的生存状态有关,就像海上迎着风浪的一条小船,焦虑多于智慧的威严。他可能是启蒙运动的后裔,不是马克思式的启蒙者,尽管他不想主宰、规训和惩罚任何人,但他犹如身穿蓝灰色屠宰衣,在市场街的肉案上霍霍地磨着屠刀,这刀锋上的文字,检验出心灵的壮阔。他厌倦了人间的虚伪,这厌倦何其旺盛,就像他少年时代的黑胡子一样疯长,这使他的散文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
在当代中国散文界,我关注着何述强、格致、扬献平、凌仕江、扬永康等青年作家,也关注着被称为“江西散文三骑士”的江子、傅菲和范晓波。在这批青年作家中,江子的写作是坚决而果断的,他所表现出的审慎、犹疑和矛盾,既是他用文字的热泪,对粗暴世界观的反讽,又是他个人伤口的经验,这使散文的思想内涵和人性内涵更浑厚,更具魅力的表证。作为一种暗示性反讽,江子面对乡村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故乡的解构也毫无疑问,只是一种温柔的解构,与他父亲的暗疾相呼应,把父亲的怯魅还原和日常化,而且病得也是不明不白。他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在追怀一个特殊的时代,张扬一种野性的有血气的生命,不如说是在借父亲的暗疾来批判政治、历史和人性的黑暗,完成了由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乡村本身的解构。随之而来的,是价值体系的崩溃,父亲的暗疾与逐渐的缺席状态,就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崩溃。读江子的散文,你可以感受他对自我价值的迷惘,对爱情、伦理、道德和意义的怀疑,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情绪。在他的散文中,自我迷失和人性异化,个体的体验、困惑、疑虑与他独特的经历,与乡村故事紧紧迭合在一起,童年的文化印记,少年的莫名哭泣,成年的人性呼喊,甚至在身体的每一次疼痛体验中,完成了他的每一次的艰难超越。
我此时在想,江子前面是城市、交通、人群和疾病中心,城市栽培的孤独,正在长出远离故乡的忧伤,他注定要失去故乡,一如我的故乡对我的伤害。他的《漫游者之歌》一文,让人直观地看到了生活和世界走向破碎的感性图景,他通过对人生历程的刻划,准确地勾划了自身演变的精神轨迹,也完成了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概括。我把故乡视为摔破的花瓶,固有的人性黑暗和隐藏,都像树荫下的胚芽,注定在故乡露出破绽和告别。江子的泪是止不了的,一如我左腿上的伤疼,一如童年的饥饿。江子的呼喊我藏着,江子经历的梦,也许正在敲碎我的现实。他对特殊经验的自信,有一种占有欲和精密的分析欲,想从生活的基本元素中,领会人性的复杂性,以便考验自己的人格力量,他如此艰难地求证着人性的亲合力。在《永远的暗疾》、《流浪的篾刀》、《对岸的村庄》、《医院》、《消失的村庄》等散文中,江子求征了人性的扭曲,爱情的殒落,伦理和亲情的流失,以及对故乡人的精神情绪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尤其在《从八一大道371号出发》中,表现出江子对当下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能力。以我的判断,他的妻子、女儿和故乡,一直是他灵感的唯一源泉;在他这久经风浪的心底,仍时常激荡着他的初恋。但是在故乡之外,他的心开始衰老了,因为他过早地遇到了新的风暴,并从多次的险境中逃脱,他怎能不抒发这种逼迫呢?然而,江子的生存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在都市中失语,生存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故乡的根基正在崩溃。这是一种悖论性的生存处境,是他对尴尬生存的隐喻,也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哲学思考。
在散文叙事方面,江子体现了独特的追求,他借博尔赫斯的思想资源,喜欢本色的、生活化的、波德莱尔式的叙述风格,他对原始的自然情感的表达,显得更为心平气和,难见那种折磨他的焦虑感和自卑感。他从乡村中来,到城市中去,从命脉里还要回到泥土里去,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注满莫名的恩怨。江子的散文,也注满自我热情,这是为了凸现个人的内心体验,他甚至常常以自传的方式,直接呈现私人经验,解剖个人的生命体验。他在解构故乡的同时,采取的是冷漠、俯瞰和超越的情感。在《一个人的火车》里,江子毫无保留地呈现自我的情感、体验和欲望,坦露自身隐秘的心态,时刻在场和现身,仿佛他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这是他的叙事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保证。从南昌到吉水,或者从吉水到南昌,要路过九个车站,他也许遭遇过九种力不从心的事,跟九个姑娘有过经典邂逅,但在破旧而拥挤的车厢里,任何稳定的信条、规范和准则的存在,都变得日益困难和不可信。他从吉水的一个小镇,调到省文联后写的散文,总是具有强烈的切肤之痛,他对当下的时代情绪,对人生世态的捕捉,也是原生态和直观化的,一切均被他打开,秘密和伪装全被他戳穿,给读者一种毛茸茸的阅读感受。对江子来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这种把生活和艺术同构化的好玩之性,如同他的坦率、真诚和自由,催生了一种无所顾忌的透明的叙事风格,他试图借此建构一种崭新的世界图式(如《血脉里的赣江》)。他就是这样,用牙齿般的文字,用打台球的心态,思考一生的问题。他用回忆消愁,用城市的前途,截断乡村的退路,用春天的鲜花与绿叶,遮住心中的孤独与忧伤。
马季曾对我说,意识形态的语言禁忌,正是对语言表现力的一种文化阉割。我对马季说,把这种命运比作大脑淤血,把挫折当成神经病之后,才能把悲哀的债务彻底还清。江子也是这样发闷发呆,发出痛苦的叹息,并在痛苦中酝酿着一场文学的绝症。所以说我没有被阉割,江子也没有被阉割,他的散文语言和结构,采取的是自然主义态度。他喜欢语言的日常化,故事的生活化,这是他基本的艺术策略,他是在还原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这使语言本身具有了温度、情感和野生的表现力。换句话说,这种散文语言正是一种与故事、人生和世界相契合的语言,这种绵长而伤感的思绪,有着反散文的写作行为。他有随心所欲的姿态,没有束缚,也没有顾忌,遵循一种打台球式的思维,既没有刻意的结构,也没有宏观的设计,但他找到了写作的乐趣,也呈现了散文探索的可能性。
我和江子没有两样,一生都在痛苦中模拟欢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孙子和儿子,做他人的好学生,做好丈夫,做优秀父亲,还做那被制度阻隔的白日梦,一生都在诺言中迁徙漂泊。基于此,江子热衷于生活流式的结构,一篇散文的展开,就是一段生活和人生的展开。他的《永远的暗疾》有一种对人性温亮的绝望的寻找,就像父亲一生都在守望中舔起旧伤口。在《侏儒》和《色盲》等散文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或对自己的残酷,或对世界视若无睹,就像对花草不屑一顾,一生都在反省中拒绝悔悟。这就是江子讲的故事,暗含着某种真象与假象、正常与病态、真实与荒诞的悖论关系。尤其是房东给江子讲的故事,成为一个精神慰藉者的结局,饱含着巨大的反讽力量。江子以写实的方式表现荒涎,以写实的方式传达寓言意味,他对现代人精神困境和病态人格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显示出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跟江子打球的时候,我们突然蠢蠢欲动,让彼此吃惊,然后又镇静,打消念头,猛地想起故乡,又沮丧地从故乡逃走。在鲁迅文学院,我和江子就是这样困顿和疑惑,处在脑筋僵硬的状态。可是我没想到江子的散文,是相当成熟的散文,厚实凝重的内涵,新颖的艺术探索,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标志着创作的一个新高度。我想他是建设者,又是摧毁者,他也许让文坛不得安宁。也许他在打台球中被淘汰,在碌碌无为中被迫离开文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理解江子的写作态度,哲学内蕴和精神思绪,弥漫在散文的每一寸空间,这使他对笔下的人物、场景和时代有充分的自信,因而叙述起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很见艺术功底。我说的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对江子来说,也许他一生都在精神迁徙漂泊中,饱尝写作的悲哀。他对散文风格的探索,还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和成熟的过程中,也许源于一种艺术的惯性,他的想象空间和通道,注定会得到丰富与开拓,好在江子还很年轻,在爱与被爱中尽情地爱,犹如回忆妻女的温馨,在幸福中饱尝果实的快乐。